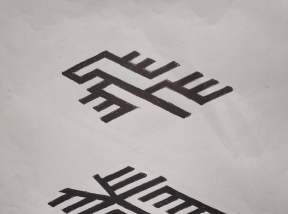自中國“新詩之父”胡適始用白話文吟詠月夜算起,中國新詩已歷百年。

研究新詩的謝冕先生已有87高齡。
“我的季節(jié)已屆深秋。然而我依然迷戀人間的春花秋月,依然尋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謝冕等待著詩人們能像百年前新詩興起時一樣,再赴春天的約會。他把這一等待作為新作《中國新詩史略》的結(jié)語。
新作逾40萬字,從起筆到付印,前后將近20年。謝冕寫得很慢很慢,他既要鉆入一首首新詩誕生時的微觀生態(tài),又要把它們放入歷史的景深,描繪它們投給當(dāng)下的背影。他的筆端泌出熱情與冷峻、敬仰與體諒、喜悅與哀傷的脈脈細(xì)流,淌過新詩來時路。這一路,有披荊斬棘、雷霆萬鈞,有一地雞毛、萬馬齊喑,有光風(fēng)霽月、春暖花開。筆觸與史實(shí)這般滲透,令《中國新詩史略》成了一部觀點(diǎn)鮮明又飽含溫情的書。謝冕曾言“落筆不敢妄言”,他10多年前的落筆,依然能像水溶于水一樣化入人心。
原本以為,在新詩百年之際,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在他的新作完成之際,新詩是他最樂意談的話題。他卻淡淡地說:“研究新詩只不過是我的職業(yè),我的愛好;我更看重的是我的生命如何安排,人生如何選擇。”
一片冰心溶入幼小的血脈
恐懼伴隨著謝冕的幼年時光:因敵機(jī)轟炸而舉家逃難,因逃難而頻繁換小學(xué),因父親失業(yè)交不起學(xué)費(fèi)而一度失學(xué)撿稻穗,因沒有糧食而不知道下一頓飯在哪里……
生活如此無望,母親卻從容迎接著每一個黎明:晨起細(xì)細(xì)梳妝,在發(fā)髻上邊插一束鮮花。
除了這一束鮮花,讓謝冕從黑暗中看到一縷亮色的,還有冰心的《寄小讀者》。
“童稚的心靈中,宛若吹進(jìn)了一陣清婉的風(fēng)。”《寄小讀者》為謝冕開啟了瑰麗夢境,他看到了太平洋舟中斜陽映出的波光,看到了慰冰湖四圍的秋葉,看到了深山萬靜之中、病榻旁的友情和鄉(xiāng)思,看到了凝聚于大自然綺麗景色中的萬種柔情……他驚嘆道:“文學(xué)竟有這般奇能,它揭示和再現(xiàn)世間萬物的奧秘,它昭告人們,世界有著難以曲盡的美麗與豐富。”謝冕默默記誦,潛心領(lǐng)會,讓一片冰心溶入幼小的血脈。
《寄小讀者》含29篇書信體散文,是冰心在1923年至1926年旅美期間陸續(xù)撰寫的。赴美前夕,就讀燕京大學(xué)的她出版了姊妹篇詩集《繁星》《春水》,它們分別集納了164首和182首小詩。這些小詩是1919年起隨手記下的思想靈光。這一年的五四運(yùn)動直接支持和導(dǎo)引了中國始自晚清的詩歌變革,新詩革命成為“五四”新文學(xué)革命的組成部分和先鋒。
一百年過去,謝冕在《中國新詩史略》第二章“鳳凰涅槃”中,將詩體大解放之初的積極探索漸次呈現(xiàn)。他說,“這是一個彰顯個性的年代”“‘五四’初期小詩運(yùn)動的流行,正是這種詩人轉(zhuǎn)向自我表達(dá)的體現(xiàn)”“冰心是最集中寫小詩的一位”“傳統(tǒng)的格律和形式的束縛在這里徹底地解除了,清新明朗,蔚為一時之盛”。
冰心青年時代學(xué)習(xí)、生活過的燕大校園,后來成了謝冕學(xué)習(xí)、生活的北大校園。他倆祖籍都是福建長樂,謝姓有很多家堂號,他們都屬“寶樹堂”。謝冕偶爾帶著家鄉(xiāng)人去探望冰心。“她送我一張照片,在背面簽名,筆力強(qiáng)勁寫下‘謝冕同……’。我在邊上看她寫到這里,就猜,同學(xué)?同志?同鄉(xiāng)?沒想到她寫的是‘謝冕同宗’!快100歲的老人了,思維還那么清晰,用詞還那么講究!”
冰心先生帶給謝冕的精神慰藉,是貫穿生命始終的。每當(dāng)冰心看到謝冕文章中流露出的悲觀情緒,她就要指出來:“這不好……”謝冕對這位一直陪伴自己成長的摯友和良師傾吐著感恩之情:“愛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撒種,隨時開花,將這一路長途,點(diǎn)綴得香花彌漫。使穿枝拂葉的行人,踏著荊棘,不覺得痛苦,有淚可落,也不是悲涼。”當(dāng)《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成為一代代少年的手邊書,謝冕說出的就不只是他一個人的心聲。
第一次莊嚴(yán)選擇:穿上軍裝
“冰心教我愛,巴金教我反抗。”這兩位文學(xué)大師為謝冕的童年鑄魂。
讀中學(xué)時,謝冕組織了讀書會。從茅盾的《幻滅》《動搖》,到巴金的《滅亡》《新生》《家》,他有了更廣泛、更有目的的閱讀,并有了獨(dú)立的思考。
戰(zhàn)亂和動蕩,餓殍和傷殘,流離和貧窮,帶給他早熟的憂患,他在黑夜呼喚黎明。
1948年11月,他將課堂作文《公園之秋》投寄給報紙,不幾天就被刊登了出來。“風(fēng),像一把利刀,刺向人民的咽喉,哀呼一聲,血流出來了,人民哭了,哭聲恰像秋的風(fēng),颯颯地響。憂郁的山啊!你皺著眉,屹立在對面,泉水潺潺地從山凹中流下來了,是孤獨(dú)者的淚啊……”朦朧的反抗意識和沉痛的文字,出自這位16歲少年。
謝冕渴望改變現(xiàn)狀,思想傾向革命。他陸續(xù)參加了學(xué)生的進(jìn)步運(yùn)動,從同學(xué)和老師那里,閱讀了由香港轉(zhuǎn)入內(nèi)地的解放區(qū)的作品,如《白毛女》《白求恩大夫》等。國統(tǒng)區(qū)流行一首歌《山那邊喲好地方》,“……萬擔(dān)谷子堆滿倉……年年不會鬧饑荒……窮人富人都一樣,你要吃飯得做工喲,沒人給你做牛羊……”謝冕一聽,“這太好了,山那邊人人平等,都能吃上飽飯,這不正是我向往的世界么!”
1949年3月,在國民黨的高壓中,正讀高一的謝冕在報上發(fā)表了詩歌《見解》:“淚是對仇恨的報復(fù),/鎖鏈會使暴徒叛變,/法律原是罪惡的淵藪,/冰封中有春來的信息。//黑夜后會不是黎明?/有人在冀企著春天!/歷史的車輪永不后退,/寂然的山火孕有憤怒的火焰。”年輕的謝冕“一心一意要通過詩喊出人民的聲音”。在一首題為《詩》的詩中,他確認(rèn)詩應(yīng)當(dāng)“呼喊出奴隸的聲音/是被損害與被侮辱者的咆哮”。
這年暑假,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福州。槍聲稀疏之后,大街兩旁睡滿了長途行軍作戰(zhàn)而疲憊不堪的戰(zhàn)士。“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啊!他們是勝利者,他們有理由享受他們以鮮血和汗水換來的一切,但他們就這樣直接躺在夏季的陽光直接照射的大街上。”這一嚴(yán)格自律而秋毫無犯的義師形象讓謝冕激動不已。他們解放了他,他要加入他們的隊伍,去解放更多像他一樣受難的父老鄉(xiāng)親、兄弟姐妹。
當(dāng)解放軍文藝工作隊的一位干部來到謝冕的學(xué)校動員參軍時,謝冕毫不猶豫做出了人生中第一個莊嚴(yán)的選擇。1949年8月29日,17歲的謝冕穿上了軍裝。他向報刊投寄了中學(xué)時代的最后一篇文章《我走進(jìn)了革命的行列》:“……不再留戀家的溫馨、父母的愛……去愛人民,去愛祖國,去扛起槍桿……唯有革命,才有我們完全美滿的家,才有各人安定的生活……我走進(jìn)了革命的行列,我滿心充沛著喜悅!”
從軍6年間,謝冕做過文工隊編導(dǎo)組副組長、文化教員、土改隊員、軍報記者、海島駐防戰(zhàn)士……直至1955年4月奉命復(fù)員,回到福州。第二次莊嚴(yán)選擇:考入北大。
8月29日這個日子對謝冕來說意義特殊,這意味著他人生的兩次重大轉(zhuǎn)折:1949年的這一天,他走入了軍營;1955年的這一天,他走進(jìn)了北京大學(xué)。
高考填志愿可以填3個,謝冕都填了:北大、北大、北大。他說:“我就知道北大好。我進(jìn)了北大才知道,它竟然有這樣好!”
謝冕加入了北大詩社。他用一首題為《一九五六年騎著駿馬飛奔而來》的小詩來迎接他在北大的第一個新年,“在北京大學(xué)的未名湖畔/我也聽見一九五六年的腳步在響/雖然冰霜封凍著大地/可是我的心卻燃燒得發(fā)燙/祖國的每一天都不平凡/新來的年度又是這樣的充滿陽光/我要不虛度每一個有意義的時日/像勤勞的工人農(nóng)民那樣”。
除夕之夜,大飯廳的舞會舉行到夜闌。零點(diǎn)零分,舞步停下來,未名湖邊的鐘聲響了。馬寅初校長微醺著向大家拜年,最讓謝冕記憶深刻的,是校長那一句“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幾杯酒”。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政治局?jǐn)U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guān)系》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此后的一年間,在《中國新詩史略》中被謝冕稱之為新詩的“百花時代”。它夢幻般美麗,終又在之后的一次次疾風(fēng)驟雨中,凋零、荒蕪。
暴風(fēng)雨過后,詩人們終于等到了悲喜交集的歸來。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了帶著滿身傷痕歸來的艾青的《紅旗》:“火是紅的,/血是紅的,/山丹丹是紅的,/初升的太陽是紅的;//最美的是/在前進(jìn)中迎風(fēng)飄揚(yáng)的紅旗!”艾青曾于1938年創(chuàng)作了《我愛這土地》,詩中那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既為當(dāng)時的抗戰(zhàn)擂響了鼓點(diǎn),又穿越時空令今天的人們動容。謝冕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在新詩的發(fā)展史上,胡適是光輝的起點(diǎn),郭沫若傳達(dá)了‘五四’時期的浪漫激情;而中國白話新詩文體的完成則是艾青。”曾以沉郁內(nèi)涵和自由形式創(chuàng)造了詩美奇觀的艾青,躲不過“疾風(fēng)驟雨”,直至用《紅旗》迎來改革開放的春天。
艾青將歸來之后的第一本詩集,定名為《歸來的歌》,該書于1980年5月出版。幾乎同時,謝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在詩壇引發(fā)震蕩。謝冕在文中支持了當(dāng)時引起激烈爭論的“朦朧詩”,主張對新的探索“適當(dāng)?shù)娜萑毯蛯捄辍保虼吮环Q為“崛起派”。時至今日,“朦朧詩”掀起的新詩潮帶給中國社會的巨大沖擊,正逐漸被歷史所接納和認(rèn)同。今天的人們,誰不能隨口說出幾句舒婷、顧城等“朦朧詩派”代表詩人的經(jīng)典詩句呢——“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云里”“仿佛永遠(yuǎn)分離,卻又終身相依”“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當(dāng)詩人們或文藝評論家們?yōu)樵姷幕ㄩ_花謝、葉枯葉榮噓唏、爭論、贊美時,唯有未名湖像接納倒影一樣接納所有,再漾起一泓清波。從沙灘紅樓和未名湖畔走出了胡適、魯迅、聞一多、劉半農(nóng)、徐志摩、冰心、馮至、沈從文……究竟是紅樓的鐘聲和未名湖的清波濡染了他們的靈思,還是他們的靈思蕩滌了鐘聲與清波?
謝冕愛這未名湖。“我們認(rèn)定了這湖,再多的美景也抵不過它,它們加起來也不能把這湖從我們心中換了去。”他喜歡繞湖而行,是一種習(xí)慣,一種享受,一種儀式,從初春直到深秋,從弱冠直到耄耋,從相許直到相守。他說:“北大是我精神的故鄉(xiāng)。”
詩人的在場給了新詩以信心
新詩潮、后新詩潮漸次退潮。
上世紀(jì)90年代,“下海”“出國”頗為時髦,物質(zhì)的豐裕與精神的匱乏構(gòu)成了巨大落差,詩似乎正離我們遠(yuǎn)去。謝冕在一篇篇文章中發(fā)出警醒:“它不再關(guān)心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它們用似是而非的深奧掩飾淺薄和貧乏。當(dāng)嚴(yán)肅和誠實(shí)變成遙遠(yuǎn)的事實(shí)的時候,人們對這些詩冷淡便是自然而然的。”“詩人沉湎于個人的‘內(nèi)心’,而這所謂的‘內(nèi)心’是與世無涉的。它過于冥想,似乎有什么禪機(jī)或哲理,其實(shí)多半是迷狂的自戀。”“這一切的背后,是對詩的思想含量和精神價值的輕忽。”
2000年底,謝冕飛赴大連,參加20世紀(jì)最后一次詩歌聚會。風(fēng)雪嚴(yán)寒,大連機(jī)場跑道封凍,全國的詩人們和文藝評論家們分別取道沈陽、青島、煙臺等地,輾轉(zhuǎn)抵達(dá)。
如同詩人們抵抗封凍,新詩亦在抵抗陷落。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汶川大地震。《生死不離》和《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通過手機(jī)迅速流傳。“……生死不離/我數(shù)秒等你消息/相信生命不息……無論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脈能創(chuàng)造奇跡/你一絲希望是我全部的動力”“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媽媽怕你,碰了頭/快,抓緊媽媽的手/讓媽媽陪你走……”詩人們不再囈語,喊出了千萬人的心聲。
汶川大地震,玉樹大地震,北京奧運(yùn)會,世博會,共和國60周年……在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淚水和歡笑構(gòu)成了絢麗多彩的詩歌畫卷,短章長句競相出現(xiàn),蔚為大觀。謝冕欣然道:“詩人沒有缺席,他們的在場給了新詩以信心。”
詩人們也在反思自己的創(chuàng)作,調(diào)整自己的姿態(tài)。在處理個人寫作與公共關(guān)懷方面,謝冕尤贊同詩人王家新的觀點(diǎn):“一個詩人既要堅持一種寫作的難度,不向任何時尚和風(fēng)氣妥協(xié),堅持按照自己的藝術(shù)標(biāo)準(zhǔn)來寫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種對歷史、人生和靈魂問題的關(guān)懷。只有這樣,它才能具有某種‘公共性’,它才會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謝冕說:“歷史上所有的偉大詩人都不會陶醉于自我撫摩而遠(yuǎn)離人間的大悲哀、大歡樂。對于詩人而言,為自己所處的時代、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乃至為人類的命運(yùn)而書寫和吟詠從來都不意味著羞恥。”他列舉了每一個時代的代表性詩人:“五四”時期有郭沫若,抗戰(zhàn)時期有艾青,大后方有穆旦和他的朋友們,解放區(qū)有李季和阮章競,20世紀(jì)50年代有郭小川和賀敬之,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有舒婷、海子……當(dāng)“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成為上世紀(jì)末的絕響,謝冕在等待新世紀(jì)更動情、更能穿越時間的詩歌。
在用等待作為《中國新詩史略》的結(jié)語之前,謝冕抄錄了2010年上海世博會志愿者主題歌《世界》的歌詞(王平久作詞):“一個擁抱 一個世界/你的世界是我們的擁抱/擁抱很大 很小的世界/世界很遠(yuǎn) 很近的擁抱//一個微笑 一個世界/你的世界是我們的微笑/微笑有情有愛的世界/世界有澀 有甜的微笑。”
謝冕之所以引用這首歌曲,除了肯定“它的節(jié)律追求接近于我們心目中的詩”,更有感于“它建立于世界大視野的言說”。
詩中的世界,有情懷;有詩的世界,更美麗。
【人物檔案】
謝冕,1932年生,福建福州人。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現(xiàn)為北京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任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及《新詩評論》主編。2005年起擔(dān)任北京大學(xué)中國新詩研究院院長。
著有《湖岸詩評》《共和國的星光》《文學(xué)的綠色革命》《論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等十余種學(xué)術(shù)專著,以及散文隨筆集《世紀(jì)留言》《永遠(yuǎn)的校園》《流向遠(yuǎn)方的水》《心中風(fēng)景》《花落無聲》等。主編了《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10卷)、《百年中國文學(xué)經(jīng)典》(8卷)、《百年中國文學(xué)總系》(12卷)、《中國新詩總系》(10卷)、《中國新詩總論》(6卷)等大型叢書。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謝冕編年文集》(12卷)。
記者手記
謝教授,您好!
慢跑、冷水浴,一年四季不間斷。很難想象,謝冕先生硬朗的身板竟是由冰與火交替錘煉而成的。更讓人感佩的是,當(dāng)冰與火的人生經(jīng)歷壓在他這副身板上的時候,他依然風(fēng)骨錚錚又謙遜慈悲。
人們給了他詩家、作家、文藝評論家等諸多名號,他最看重的卻是他北大教授這一身份。前些日子,他被2018—2019華人教育家大會推選為“華人教育名家”。“我很怕被稱為這個‘家’那個‘家’,但這個‘華人教育名家’倒還算恰如其分。”
他把87歲的生命與綿延的新詩史相比,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我一輩子只做文學(xué),文學(xué)只做了新詩”;他把自己與學(xué)生相比,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我自己微不足道,但我的學(xué)生很了不起,個個都聰明出色,這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一點(diǎn),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點(diǎn)。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可以算‘教育名家’。”
所以,當(dāng)我們向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不妨稱一聲:謝教授,您好!
來源:文匯報 | 江勝信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