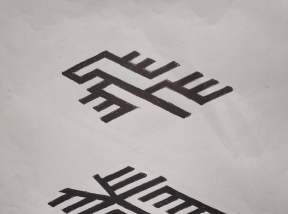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詩壇快遞 于 2020-5-4 20:40 編輯

6.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15)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5-4 20:35 上傳
我不寫詩的那些日子
多么平常的日子 詩散漫地出門 樹上云端都去走走。 詩也有它自己的事情 將軍也要度假。
守在最近處的錦衣侍者 只要我招呼 只要我抬一抬手。
過去的一年我沒有買日歷 我不寫詩的半年里 日子照樣時緊時慢地走。
沉的東西并不永遠(yuǎn)沉 沒有什么值得特別去珍貴 對于別人它什么都不是 對于我它才是詩。 昨天還是詩 今天可能就不是了。
自稱為詩遠(yuǎn)道而來的這個人
我的門前冒出一條魚 閃閃發(fā)出直立起來的水光。 他說他冒雨從激烈的東方來 和方向無關(guān)。 和日出無關(guān)。
我探身向外沒看到激烈。 閃電迎頭在上 飛一樣 誰像傻子刻舟求劍 背后深深地硌著刀刃。 我不認(rèn)識的這個敲門人 你真懷有利器 你就坦然如王地進(jìn)門說話。
他說他是為了詩 整夜整夜像荊珂趕路 小心翼翼帶著越走越沉的金子。
可是走動不代表什么。 可是我不再相信空洞的名義。
請你拿件黑膠雨衣 和你的金質(zhì)才華 回你幻想的風(fēng)暴眼里去吧。
不認(rèn)識的人就不想再認(rèn)識了
到今天還不認(rèn)識的人 就遠(yuǎn)遠(yuǎn)地敬著他。 三十年中 我的朋友和敵人都足夠了。
行人一縷縷地經(jīng)過 揣著簡單明白的感情。 向東向西 他們都是無辜。 我要留出我的今后。 以我的方式 專心地去愛他們。
誰也不注視我。 行人不會看一眼我的表情 望著四面八方。 他們生來 就不是單獨的一個
注定向東向西地走。
一個人掏出自己的心 扔進(jìn)人群 實在太真實太幼稚。
從今以后 崇高的容器都空著。 比如我 比如我蕩來蕩去的 后一半生命。
今天不好
今天的太陽好天空好 大雨洗新了滿園的龍眼樹 手卷起了軟竹簾。 但是我不好 所以今天不好。
太陽和月亮同時在天上。 是昨天又轉(zhuǎn)身回來 還是明天無緣無故地提前? 時間一定不多了 日和夜著急地擠到一起 天光多么刺眼。
如果能找到原因 我一定要先把今天變好。 然后一點點美化未來 可是滿頭戴花的龍眼樹傻站在窗前 既不快樂也不悲哀。
龍眼啊龍眼 理由不可能被看見。 只有我一個人 覺察出今天的種種不好。
月光白得很
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頭。
我呼進(jìn)了它青白的氣息。 人間的瑣碎皮毛 變成下墜的螢火蟲。 城市這具死去了的骨架。
沒有哪個生命 配得上這樣純的夜色。 微微打開窗簾 天地正在眼前交接白銀 月光使我忘記我是一個人。
生命的最后一幕 在一片素色里靜靜地彩排。 月光來到地板上 我的兩只腳已經(jīng)預(yù)先白了。
月光使人站不穩(wěn)
海正在上岸 鹽啊,攤滿了大地 風(fēng)過去,一層微微的白 月光使人站不穩(wěn)。
財富研出了均勻的粉末 天冷冷的,越退越遠(yuǎn),又咸又澀。 那枚唯一升到高處的錢幣 就要墜落了 逃亡者遍地舞著白旗。
銀子已經(jīng)貶值,就像鹽 已經(jīng)貶值。 我站在金錢時代的背面 看著這無聲的戲怎么收場。
隱藏
無意中,在店鋪門口看手里的英鎊 印著婦人頭像的紙 各種香水味道,彈起來聲音清脆。
我要緊急處理我的錢包 把那些從遠(yuǎn)地方帶過來的東西 藏得更深。
那一層層又黏又厚的血汗 忽然成了我的個人隱私 這一大疊哦,早被摸得不是錢了。
假如有人在威爾士偷竊 會不會扔掉這些骯臟的紙 被叫做人民幣的東西 只適合在人民之間傳遞。
出門種葵花
春天就這樣像逃兵溜過去了 路人都還穿著去年的囚衣。 太陽千辛萬苦 照不綠全城。
一條水養(yǎng)著黃臉的平原 養(yǎng)著他種了田又作戰(zhàn) 作了戰(zhàn)再種田。 前后千里 不見松不見柳不見荷不見竹。
我不相信 那個荷蘭人 會把金黃的油彩全部用盡。 我們在起風(fēng)的傍晚出門 給灰沉的河岸 加一點活著的顏色。
種子在布袋里著急。 我走到哪兒 哪兒就松軟如初。 肥沃啊 多少君王在腳下 睡爛了一層層錦繡龍袍。
在古洛陽和古開封之間 我們翻開疆土 給世人種一片自由的葵花看看。
喜鵲沿著河岸飛
那只喜鵲不肯離開水。 河有多長 它的飛行就有多長。
負(fù)責(zé)報喜的喜鵲 正劃開了水 它的影子卻只帶壞消息。 好和壞相抵 這世上已經(jīng)沒有喜鵲 只剩下鳥了。
黑禮服白內(nèi)衣的無名鳥 大河仰著看它滑翔。 人間沒什么消息 它只能給魚蝦做個信使。
連一只喜鵲都叛變了。 我看見叛徒在飛 還飛得挺美。
半個我正在疼痛
有一只漂亮的小蟲 情愿蛀我的牙。
世界 它的右側(cè)驟然動人。 身體原來 只是一棟爛房子。
半個我里蹦跳出黑火。 半個我裝滿了藥水聲。
你伸出雙手 一只抓到我 另一只抓到不透明的空氣。 疼痛也是生命。 我們永遠(yuǎn)按不住它。
坐著再站著 讓風(fēng)這邊那邊地吹。 疼痛閃爍的時候 才發(fā)現(xiàn)這世界并不平凡。 我們不健康 但是 還想走來走去。
用不疼的半邊 迷戀你。 用左手替你推動著門。 世界的右部 燦爛明亮。 疼痛的長發(fā) 飄散成叢林。 那也是我 那是另外一個好女人。
很多很多的花很多很多的菜
每天勞動 讓這小塊土地不一樣 這個春天造了三個世界 很多的花和菜的世界 還有粉蝶的世界 蚯蚓的世界
如果戰(zhàn)亂來了 可以割香茅做掩蔽 饑荒一到就改種糧食 只要一個下午 去翻開泥土 人間就是迷戀循環(huán)的游戲 嘿,壞日子 簡直是在盼著了
懸空而掛
犯什么重罪 它們被絕望地懸掛? 高懸 那些半空中隨風(fēng)飄蕩的物體。
沒有眼睛的等待。 雨傘。海棠。 花盆。老玉米。
我害怕突然的墜落。
我要解放你們于高懸。 在我這兒 懸掛就是違反了我的法律。 我要讓萬物落地 我在海洋以外的全部陸地 鋪曬羔羊的軟毛。 接住比花粉更細(xì)微的香氣。 讓野獸,像溫泉 貼著鞋底緩走。 我看見日月 把安詳?shù)墓鈸渖⒃诘孛?/div> 世界才有了黑白 有了形色。
整個大地 因為我而滿盈。 像高矮不同的孩子們 席地而坐。
我紅亮的珠寶還在蹦跳。 它現(xiàn)在落地為安。 我正用疏松的手 摸過萬物細(xì)密之頂。
白紙的內(nèi)部
陽光走在家以外 家里只有我 一個心平氣坦的閑人。
一日三餐 理著溫順的菜心 我的手 飄浮在半透明的百瓷盆里。 在我的氣息悠遠(yuǎn)之際 白色的米 被煮成了白色的飯。
紗門像風(fēng)中直立的書童 望著我睡過忽明忽暗的下午。 我的信箱里 只有蝙蝠的絨毛們。 人在家里 什么也不等待。
房子的四周 是危險轉(zhuǎn)彎的管道。 分別注入了水和電流 它們把我親密無間地圍繞。 隨手扭動一只開關(guān) 我的前后 撲動起恰到好處的 火和水。
日和月都在天上 這是一串顯不出痕跡的日子。 在醬色的農(nóng)民身后 我低俯著拍一只長圓西瓜 背上微黃 那時我以外弧形的落日。
不為了什么 只是活著。 像隨手打開一縷自來水。 米飯的香氣走在家里 只有我試到了 那香里面的險峻不定。 有哪一把刀 正劃開這世界的表層。
一呼一吸地活著 在我的紙里 永遠(yuǎn)包著我的火。
一塊布的背叛
我沒有想到 把玻璃擦凈以后 全世界立刻滲透進(jìn)來。 最后的遮擋跟著水走了 連樹葉也為今后的窺視 文濃了眉線。
我完全沒有想到 只是兩個小時和一塊布 勞動,居然也能犯下大錯。 什么東西都精通背叛。 這最古老的手藝 輕易地通過了一塊柔軟的臟布。 現(xiàn)在我被困在它的暴露之中。
別人最大的自由 是看的自由。 在這個復(fù)雜又明媚的春天 立體主義走下畫布。 每一個人都獲得了剖開障礙的神力 我的日子正被一層層看穿。
躲在家的最深處 卻袒露在四壁以外的人 我只是裸露無遺的物體。 一張橫豎交錯的桃木椅子 我藏在木條之內(nèi) 心思走動。 世上應(yīng)該突然大降塵土 我寧愿退回到 那桃木的種子之核。
只有人才要隱秘 除了人 現(xiàn)在我什么都想冒充。
從北京一直沉默到廣州
總要有一個人保持清醒。 總要有人了解 火車為什么肯從北京跑到廣州。
這么遠(yuǎn)的路程 足夠穿越五個小國 驚醒五座花園里發(fā)呆的總督。 但是中國的火車 像個悶著頭鉆進(jìn)玉米地的農(nóng)民。
這么遠(yuǎn)的路程 書生騎在毛驢背上 讀破多少卷凄涼迂腐的詩書。 火車頭頂著金黃的銅鐵 停一站嘆一聲。
有人沿著鐵路白花花出殯 空蕩的荷塘坐收紙錢。 更多的人快樂地追著汽笛進(jìn)城。
在火車上 我一句話也不說。 人到了北京西 就聽見廣州的芭蕉撲撲落葉。 車近廣州東 信號燈已經(jīng)拖著錨沉入南海。
我乘坐的是 另外的滾滾力量 一年一年南北穿越 火車怎么可能被火焰推進(jìn)?
不可能沿著噩夢往回走
怎么樣才能原路回去 怎么樣從不可能里找到緊急出口 地獄游戲怎么樣為我重開?
只要回去就能越飛越遠(yuǎn)。
冰雕的含羞草 千千萬萬的根又從身上發(fā)芽 拔不斷的毒箭又軟又韌 傷口們一觸即合。 我是一個人 又是一大片神奇的植物。
子彈穿過 我和它一起晶亮透明。 無數(shù)次我看見我確實死了 又逆著風(fēng)簌簌地活過來。 反反復(fù)復(fù)總在邊緣 黃了又綠的吊鐘花們 跳在深淵中間。
讓我再試試死到臨頭的感覺。
可是沒有回去的路。 太陽又在天花板上放出兩塊水豆腐 電視里發(fā)布黃色寒冷警告。 我醒來 看見的又是心不驚肉不跳的一天。
王小妮,吉林長春人,詩人、作家。著有長篇傳記文學(xué)《人鳥之間》,詩集《我的詩選》、《我的紙里包著我的火》等。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