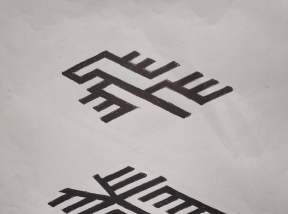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袁偉 于 2018-8-28 23:09 編輯
2016年巴西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巴西已故詩人、小說家卡洛斯﹒德魯蒙德﹒德﹒安德拉德的詩歌《花與惡心》出人意料地在開幕式上被予以朗誦。這無疑是我記事以來,從觀看西班馬巴賽羅那那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至今數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破天荒出現的唯一一次。這讓我多少有點喜出望外。在詩歌被詩歌之國的中國不斷邊緣化的今天,在異邦,詩歌可以在聚焦了世界關注目光的奧運會開幕式上出現,并向全世界展示,無疑是詩歌的榮光。我不得不以一種卑謙的態度,從頭到尾仔細端詳這朵異邦詩人開在惡心之中的花朵。 我一向對名人的頭銜遲鈍,我拿到任何大師的詩歌只有一個根深蒂固難以更改的壞習慣,那就是不看名氣,只看文本。盡管我知道,好些外語詩歌,翻譯成漢語未必有原詩那么精致準確。但是,當工業時代被信息時代的風暴卷到爪畦島上去的時候,我們的確需要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尋找到那個時代的困頓,從中把握到這位拉丁美洲詩人的思想意念脈博的跳動頻率,《花與惡心》正好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通向那個時代的路徑。馬克思說過,任何資本的原始積累都充滿了血腥。巴西,這個盛產桑巴舞,足球水平稱雄世界的國度,我對它的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是,我卻知道,這是一個世界上經濟一直欠發達的國家。但是,一切可能在其它發達國家出現的社會現象,在這里也同樣的出現了,城市、貧民窯,階層的差距,貧富的懸殊,混亂的治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頻臨崩潰的世界經濟的陰影,同樣投射在了巴西這片熱情似火的土地上,工業文明對傳統農耕文明的侵略性蠶食也一樣存在。這一切,也在蠶食詩人的靈魂。 于是,詩人一開篇,就直奔主題“被我的階級和衣著所囚禁,/我一身白色走在灰白的街道上。”“囚禁、白色、灰白”一個暗色系的詞語一經出現,我似乎就看見了詩人憂郁厭惡的面部表情。我的猜測是對的,果然,隨后的詩句向我打開了一扇扇工業文明以商品金錢衡量靈魂價值的窗戶:“憂郁癥和商品窺視著我。/我是否該繼續走下去直到覺得惡心? 這不僅僅是心理上對失去的農耕文明的失落性追溯,更是在工業文明的蠶食中徒勞的追尋。繼續走下去,因為無法讓之前完整隨后破碎的靈魂復原,惡心肯定是必然產生的生理反應。由于有這個前因,在詩中接踵而至的所有后果,即是真實,又是折射,很快便與現實結合在了一起,這不是詩意的變異,而是赤祼祼的殘酷存在。詩人反復地敘述著“時鐘里骯臟的眼睛”、“時間依然是糞便、爛詩、癲狂和拖延”、“太陽撫慰著病人,卻沒有讓他們康復”、“四十年了,沒有任何問題/被解決,甚至沒有被排上日程”,又反復詰問著,卻始終找不到讓他滿意的答案,這種敘述,嚴格說起來,應該是控訴。 一味控訴是沒有絲毫作用的。但控訴又是必須要有勇氣彰顯出來的,我個人認為,這首詩的前七節,都是一種呈現螺旋式上升的控訴與反思,到第七節,這種控訴與反思似乎到了一個極限,失去了繼續沉綿于悲哀與絕望的理由。詩人開始在批評巨浪退去之后,換了另一種眼光來觀察這個人類生息繁銜的現實社會。也是全詩沖破陳腐,迎接希望的一次跳躍性大轉折。這個大轉折出現在第八節: “一朵花當街綻放!”這是暗淡到極限的一陣狂風,霎那間就吹開了層層陰霾。在我個人看來,這也是殘存的農耕文明在詩人眼里的回光反照。這朵很丑的花,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捅破了瀝青、厭倦、惡心和仇恨,就這樣開放了,在充滿絕望的世界。這無疑是人類掙扎中一抹亮現的希望。 理解外國詩歌,由于文化傳承,思維特性,民俗風情和差異,要想從民族性和地域性來理解幾乎是徒勞的。只能從社會發展的斷代,人性的共性特點予以解析了。這樣的解析,是否牽強附會,我不得而知,但愿沒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播
轉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