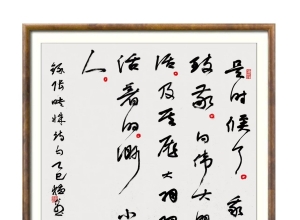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彭林家 于 2020-7-13 22:32 編輯

韓0.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2)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4-27 18:42 上傳
作者簡介:韓樹俊,江蘇蘇州人,現(xiàn)居蘇州。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報(bào)告文學(xué)學(xué)會會員、中國西部散文學(xué)會常務(wù)理事、蘇州高新區(qū)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在《文匯報(bào)》《奔流》《青海湖》《西部散文選刊》《散文選刊·下半月》《海外文摘》《時(shí)代報(bào)告》《中國高新區(qū)》《蘇州雜志》《蘇州日報(bào)》等發(fā)表作品。獲中國西部散文排行榜,中國散文年會散文集類一等獎并十佳散文獎、江蘇省主題出版重點(diǎn)出版物、蘇州市第12屆精神文明建設(shè)“五個(gè)一工程獎”,長篇報(bào)告文學(xué)《繡娘的春天》入選2018年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重大題材文學(xué)作品創(chuàng)作工程”項(xiàng)目。長篇散文《姑蘇十二娘》入選蘇州市作協(xié)2018年重點(diǎn)作家作品創(chuàng)作扶持項(xiàng)目。擔(dān)任文學(xué)顧問的歷史紀(jì)錄片《鷹擊長空陳華薰》《清華英才陳三才》在中國教育電視臺播出,擔(dān)任制片人的文化紀(jì)錄片《錦溪窯火》在上海電視臺“全紀(jì)實(shí)”頻道播出。著有散文詩集《姑蘇十二娘》《風(fēng)潤江南》、散文集《一條河的思念》、長篇報(bào)告文學(xué)《卓爾不同》《繡娘的春天》。

書韓1.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3)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4-24 18:00 上傳
風(fēng)骨吳歌情越香 ——觀讀《風(fēng)潤姑蘇》評韓樹俊的美學(xué)詩情 彭林家 “姑蘇城外寒山寺”的鐘聲,回蕩著空幽的澗谷,一任根性磁場的梵音,悅來《楓橋夜泊》的詩情綿綿不斷,暗示著城市精神的復(fù)生、蘇醒和覺悟的禪意。據(jù)歷史記載,公元前2070年的夏代叫姑蘇,隋朝開皇9 年改為蘇州。那么,別名的別腸,別出的新意,從唐代的詩風(fēng)搖拽到今天的辭筆,愁眠著一代代文人墨客的靈氣,也衍生著一種種雎鳩時(shí)空的和鳴。然而,在追尋著吳越文化的思考中,千百年的性情底蘊(yùn),無論是吳儂嬌語的盤歌,還是說噱彈唱的評彈,月落烏啼的遐思,在有限無限的回味中,“隔著青石閭巷,換成了舂谷、搗衣、石拱橋的倒影”,咀嚼著一片推敲的月色。這,別饒風(fēng)致的別調(diào),都將裊裊地從蘇州的園林里飄動,使一行行流動的漁火,幻化成一葉葉晃動的霜楓,誘我翻開《風(fēng)潤姑蘇》的吐鳳顯影,使勁地把捂熱的頁碼變幻成昨日的尺牘,驅(qū)使紆縈的靈音凝結(jié)成滌蕩的柔波,一層一層地把柔厚的文字,叩問現(xiàn)代詩家韓樹俊筆端的吳矛越劍;為水鄉(xiāng)的風(fēng)骨,氣觸一枚春秋雙璧的象征符號。 “欸乃一聲,竹篙撐出半邊天;輕舟一瀉,船娘山歌遍水鄉(xiāng)……”其文由內(nèi)意而出,當(dāng)不假取于外象之時(shí),觀讀著詩人的《船娘》:“伴隨著吳儂軟語的船歌,悠揚(yáng)著江南風(fēng)味的小唱”,一種吳越派婉約的柔曲,伴隨著夜鶯細(xì)柳的別調(diào),時(shí)不時(shí)地從鄉(xiāng)土的空間走來,帶我“穿越一個(gè)又一個(gè)石拱橋洞”,看見一個(gè)個(gè)柔情綽態(tài)的倩影,揮著竹竿,扯著喉嚨,拎起串串吳語的情歌,不經(jīng)意地從街巷穿梭,映現(xiàn)一個(gè)個(gè)劃槳撐篙的純樸印象。 北齊·顏之推 《顏氏家訓(xùn)·音辭》:“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也許是在東北師范大學(xué)念書的時(shí)候,聽?wèi)T了北派的高揚(yáng)豪邁之味,冷不丁地傾聽輕婉的聲調(diào),內(nèi)心審美的投影,便身不由己地映襯著雄闊的偉岸;爾后,又比照柔腸的蠕動,誘我左右流之,東西采之,隨時(shí)從指縫間滑下詩意的溫柔,滲透著周身的每一個(gè)細(xì)胞,甜甜地窺視作者筆下的思路。你看那:“流淌在江南小河里的船娘,如下凡的仙女一般飄逸……你穿行在水鄉(xiāng)四通八達(dá)的每一條小河里,擺渡、載物、迎送、捕撈、采摘……”。江南,曾經(jīng)在東周時(shí)期被中原稱為吳越,說的就是長江中下游;后來,隨著中原漢人大量南遷,江南漸漸成為繁榮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和美麗富庶的水鄉(xiāng)景象。如同越瘦吳肥的內(nèi)涵,撲朔迷離,撩動越瘦秦肥的意蘊(yùn)。雖然其內(nèi)在的痛癢與己無關(guān);但是,詩人見多識廣,創(chuàng)作的思維在通行于藝術(shù)同化、順應(yīng)和平衡的心靈旅程中,半池春水,一潭心境,性靈的磁化必然引起筆下的語言剛健而柔美。如:“東西南北的旅游者狂放你的船歌帶向四面八方……”在擰著心靈的轉(zhuǎn)動中,一個(gè)“狂放”的形容詞,將詩魄撓動詞骨的語境,用古典詩魂的載體,嫁接現(xiàn)代散文詩的枝葉,陰陽吮吸,互為表里,微妙地把天下無雙的吳鉤,以其肝血涂金而鑄成鉤的神魂,勾起著事物本相的原型。 “吳語有言非尺牘,友道無句是竹書”。戰(zhàn)國吳越之爭的時(shí)代,吳國先戰(zhàn)敗越國,后來,越又滅了吳,兩國均在江南接土的鄰境,其“習(xí)俗同,言語通”的集體潛意識,浸染了吳語意識行為的模仿和承襲;也是夏、商、周時(shí)期,南方夷蠻音樂聲歌的“南音”所延續(xù)的發(fā)展,才會有“同音共律”的吳愉越吟。如同“四面楚歌”替代了“四面吳歌”一樣,蘊(yùn)含著吳歌的本質(zhì)便是聲音的文化一樣,其聲韻悠揚(yáng),音調(diào)委婉,反射著楚破越之后的“吳楚”或“荊吳的擴(kuò)展潮音。察問,如此的澄懷觀道,促使著人生的藝術(shù)化和藝術(shù)的人生化,惹我了望江南窈窕的風(fēng)韻娥影,讓地域的枝葉向外伸展,蔓延著思維的遷移。假如一一反芻在詩與散文之間的縫隙里,散文詩盛開的花朵,同樣有著吳頭楚尾的韻律挪移、跳躍和波動,共振一道蝶魄的靈光。況且一切美的光源是來自心靈的源泉。由此,觀道者,必然要用審美的眼光,深深領(lǐng)悟客體具象中的靈魂生命;之后,提煉其內(nèi)在的優(yōu)勢,凸現(xiàn)一個(gè)審美客體的嶄新風(fēng)韻。比如,在凈土法門的清凈中,詩魂應(yīng)無所住而生其心,而體現(xiàn)了詩人美學(xué)的自我觀照,一任萬法由心的馳騁,上下拓展自性本能的蹉動,凸現(xiàn)一首散文詩的淳美個(gè)性。換言之,一切塵情的狀態(tài)源自于本性的變動。 那么,心靈手巧的本性則體現(xiàn)出對“美”的時(shí)空,交融著主體情感的最佳契合。你讀,《繡娘》:“枕上鴛鴦,堂前龍鳳,鏡中貓蝶,袍上花卉――以針為筆以線為墨,針針線線匯聚藝海浪花朵朵……平、齊、細(xì)、密、勻、順、和、光的諸多特色”。 一組組意象群的橫向排列,細(xì)膩情感的磁性彌漫著纖纖的十指,讓未決狀態(tài)的針磁意境,在時(shí)空的語境間隔中,留白著以情度情的經(jīng)驗(yàn)想象。那么,這種詩學(xué)的象征歧義,拓展著意象與意象的語言聯(lián)動,如同左右腦的聯(lián)合思考,以間接經(jīng)驗(yàn)的沉淀顯現(xiàn)被遮蔽的原始物像,悄然地,涌動直接經(jīng)驗(yàn)的發(fā)酵,昭彰古典意識的包涵之性,從而使“銀針在你靈巧的指尖舞動,彩線連綴起最美的畫面”等恍惚的情感,在模糊的忘我之境中,走進(jìn)以刺繡而聞名的蘇州風(fēng)情。如《琴娘》:“你用纖手撥動時(shí)代的琴弦,古箏、古琴、琵琶、弦子……委婉、輕盈、悠長,穿越了幽幽小巷……傳承了吳文化的精髓。”文本中的“琴弦”、 “琵琶”、“ 吳文化”的意象,在“穿越”的一江春水中,形成了一幅江南女子的嬌姿光影。你看,那指尖性靈的琴弦,彈出的韻味,錚錚尖音,柔柔答聲,宛如小家碧玉的越女所呼吸的氣感,使詩文的氣勢越加醇香柔靜,靈開一曲曲吳地之歌的禪情。白石道人詩說:“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從氣推血走的人體循環(huán)中,引領(lǐng)著詩歌心法的氣流,氣象渾厚為雅,體面宏大則不狂;血脈貫穿為含蓄,韻度飄逸則清晰。所謂“氣韻生動”是中國藝術(shù)的最高目的,必然要雙重表現(xiàn)著具體物象的實(shí)體和物象之外的虛空,形成內(nèi)順觀道,外扶教門的審美時(shí)空。因此,一實(shí)一虛,創(chuàng)作者,需要不斷地把顛覆語言的成規(guī),扭轉(zhuǎn)符號的新鮮感、陌生化和生命力,使三心二意的靈性本體復(fù)醒自我的創(chuàng)造力,才能在虛實(shí)結(jié)合中,返照一個(gè)散文詩人的審美三性(精、氣、神)、五法(仁﹑義﹑禮﹑智﹑信)、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的綜合素質(zhì),虛靜自我個(gè)性化的風(fēng)格。“虛”是欣賞者被引發(fā)的想象,“實(shí)”是藝術(shù)家所創(chuàng)造的形象。由此而言,詩人筆端的吳越同舟,籌劃著心靈的波流,一浪一浪地,為我們洞開一扇煙花江南的風(fēng)景窗口;抑或隱喻時(shí)空,憶念古代越國多出西施一樣的美女:“有一副好身材:修長挺拔;有一張好容顏:潔白柔嫩……今天人們稱你’茭白’,其實(shí),菰、茭瓜、茭筍都是你的名字。”(《茭白》)。要不,怎么會吃著靈性的植物,咬著情感的筆頭,一會兒就能感受到街巷阡陌的小橋流水,在身邊潺潺地依偎;一會兒又幻覺成私家園林的水池、亭臺和樓閣,撓癢生命心動的吳地風(fēng)情。私問,那文的氣象,性的體面,情的血脈,質(zhì)的韻度,一一在蘇州的風(fēng)水文化里,天挺神武,蕩漾著地方風(fēng)俗的幽靈。至今,那吳歌奏響的情絲伴隨著“美人計(jì)”的囈語,裊裊娜娜,說話極柔的音色,逐漸變相成:“當(dāng)夏日的熏風(fēng)吹起,蘇州城郊的大塘里,荷花朵朵,荷香陣陣。作為地下莖的糖藕藉著陽光瘋長,采起,洗凈,如白嫩嫩的娃。”(《蓮藕》)。江南小調(diào)的吟唱,讓音品音質(zhì)的詩心流痕,通過“娃”的意緒指代,將沿著“吳故都在館娃宮側(cè)”的西施小舟,反饋集體文化的遺風(fēng)余象;點(diǎn)燃一幕幕的姑讎帆影,穿越吳歌江南的河流,從眼前的魚米之鄉(xiāng),悠然地劃過吳娃越艷的斑駁靈痕。 從美學(xué)流程而言,詩人“自我”靜觀萬象,洞察詩品具有更高的深層結(jié)構(gòu),讓夢的潛意識無意觸動客體而連接著象征的物體,使渾然超脫自我的移情,變成“超我”的平衡,圓融成永恒的 “本我”而驀然回首,達(dá)到理想的追慕。如:“碧綠,圓整,緊貼水面荷葉一般碩大無比的葉,一直鋪展到水的盡頭……你那深藏不露的根一直堅(jiān)守在水下,日夜吮吸著陽光與水的養(yǎng)分。”(《雞頭米》)。其中的“葉”、“根”都是同物之境,物我兩忘,物我不分,自我設(shè)身于物而分享其內(nèi)的生命;一任“堅(jiān)守”、“吮吸”的動詞翹望,人情和物理的意向,相互滲透而自我不覺其滲透,如恍悟的浮現(xiàn)境界,是無我的心魂與外物合而為一。表現(xiàn)在我心無質(zhì),如臨水照花;我心無形,如云影舒卷;其內(nèi)在的眼中沒有我之得失,外在的行為沒有喜怒好惡;一顆平靜永恒的詩心,活生生地把“情”隱之于“性”的涵蓄之中,等于把一切“色”看成了“空”的境界。

書韓2.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2)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4-24 18:00 上傳
事實(shí)上,不管是散文詩還是現(xiàn)代詩,意境和意象都需要要求主客一體,抵達(dá)物我交融的合一化境。或者說,其心理狀態(tài)都是主體和物象碰撞時(shí)所形成的果實(shí),孕育著“情”的釋放歸功于“性”的本源。所謂的“聲聞覺醒他非色,證果方知我是空”。也就是自性與時(shí)空的統(tǒng)一,表現(xiàn)著性的能量與情的效果具有一致的等量齊觀。清·況周頤《蕙風(fēng)詞話》:“或帶煙月而益韻;托雨露而成潤;意境可以稍變;然而烏可等量齊觀也。所以,從沒有雜念而不消耗外力做功的情況下,本質(zhì)才能靠近相通,如同康德純粹自我意識學(xué)說,詩情才能源源不斷地從我執(zhí)識的掙脫中,感應(yīng)詩性本體的盈盈芳香。 那么,就現(xiàn)代詩歌而言,很多情況下是不一樣的層次概念,所達(dá)到的廣度與深度有著高與低的區(qū)別。一則,意境是審美的深度,其空間尺度偏于縱向磁力,表現(xiàn)在韓樹俊的《指縫的溫柔》:“纖纖十指將一頁素箋捂在胸間/微閉著眼眸把思念寄向遠(yuǎn)方……緊裹的襟懷拱起酥軟的抹胸/蠕動纖細(xì)的腰肢/塵襟思念的一鈕扣/惹起開擺的股骨/一次次地收斂大眾的目光/溫柔著無處不在的溫柔……指縫中的淚水,滴落/江南女子的喃喃蜜語”。顯然,詩中的“捂”、“寄”、“拱”、“惹”、“ 落”等一連串的動詞意緒,營造成思維挖掘本能的縱深境界。從情濃性淡為美的角度,讓“十指”、“胸間”、“腰肢”、“淚水”等形象意識的聯(lián)動,在潛意識的反射中,以意境為主,意象為輔,強(qiáng)調(diào)景物在人們心里喚起陰影情節(jié)的反應(yīng),追求言盡而意亦盡的透徹;或以“幻覺”、“夢境”等非理性狀態(tài)的隨性隨意,在激越的奔放中,浮出多層面、多維度的“再現(xiàn)”詩魂。其創(chuàng)作的心法摻入了西方文化內(nèi)在直覺思維方式的歧義,以點(diǎn)帶面,采用直觀、線性的“原型”的思維方式,直抒胸意的表達(dá)性情局部的怨氣,靠近于一種“再現(xiàn)”內(nèi)心潛意識的創(chuàng)造;如同西方的典型說,屬于情生性,性生情,情生道,道生情的循環(huán)過程,成為詩歌的縱向張力。二則,意象是審美的廣度,其空間尺度偏于橫向磁力,表現(xiàn)在韓樹俊的《閨閣的本意》:“了望對門的安樂椅/有一個(gè)狗狗的臥床/或者貓咪的食盆。猜想/壁櫥里的每一條絲巾/軟軟的席夢思床罩……你,打開臺燈滿室彌漫柔和的光影/你,端起咖啡滿室飄蕩嫻靜的暗香……畫家說,指縫中的種種顏色/是那抬頭一束向日葵的溫馨”無疑,詩中的“望”、“想”、“打”、“端”、“抬”等一連串的動詞意緒,營造成思維間隙的空白,形成橫流的逼真境界。從性濃情淡為美的角度,讓“臥床”、“ 絲巾”、“ 光影”、“ 向日葵”等形象意識的潮動,意象為主,意境滯后,平鋪在一個(gè)畫面空間里,構(gòu)成一種向度遼闊的時(shí)空格局;為大千世界的物象相通、相融和置換,促使心靈的性情,開辟了抽象、綜合的理想“模型”空間。其創(chuàng)作心法的“表現(xiàn)”詩魂,摻入了傳統(tǒng)文化外在直覺思維方式的含而不露,以面帶點(diǎn),利用質(zhì)點(diǎn)的思維方式,曲折纏綿的表達(dá)性情整體的芳?xì)猓咏谝环N“表現(xiàn)”內(nèi)心意識的創(chuàng)造,如同古典式的意境說、教化說;屬于性生情,情生道,道生情,情生性的循環(huán)過程,成為詩歌的橫向張力。 散文詩是一種音樂旋律的釋放,其語言空隙留白生成的音符。在五行氣流的中和里,詩人把“土”的自我本“道”屬性,如性柔、滋潤、包融,統(tǒng)領(lǐng)金、木、水、火的氣流,形成“德”的詩歌之術(shù),以簡約勾勒的敘述,波動水鄉(xiāng)的湖面,引誘著吳歌潛意識的聲音,輕盈柔美著一方水土的良知,促使人性情結(jié)的自性芳香,沉沉地,祭拜歷史的靈芝生長在道德的長廊上,覺醒自我的言行相詭或抱一。 因此,當(dāng)我讀到《太湖,編織時(shí)光迷離的夢幻》:一曲漁歌,百轉(zhuǎn)千回的柔腸,醉倒……滿湖的水閃耀出粼粼的波光,滿艙的魚凝固了張揚(yáng)的華麗,滿心的夢幻化為眼前看得見的喧鬧太湖,編織著時(shí)光迷離的夢幻……這樣力量的符咒,好比心情煩躁的時(shí)候,就能感覺成一縷清風(fēng)徐徐吹來,成為意識過偏或態(tài)度補(bǔ)償?shù)木裰委煟瑥摹氨憩F(xiàn)”到“再現(xiàn)”的雙重交融,浮現(xiàn)土地、田野和池塘的詩學(xué)對等原則,其歷時(shí)性與共時(shí)性的審美坐標(biāo),就如詩人的“斗笠。蓑衣。漁翁撒出舞動的彩練。驚起了水鴨,驚飛了水鳥,驚醒了水岸邊的”(《漁網(wǎng),舞動的彩練》)。文本的氣象通過“驚醒”一詞,把生態(tài)植物的表情幻覺成當(dāng)代中國人西方化的表情,讓一片“日出江南紅勝火”的情景,鑲嵌著一縷縷似水的柔慈,攪拌著輕歌曼舞的采蓮曲,一閃一現(xiàn)地穿越風(fēng)中的娉婷;一靜一動,又把陂塘的物象墜入心象的圖畫。你看:“余暉。秋水。暮歸的漁歌攪出一江金波……;魚舟的雙槳,咿咿呀呀--,劃出一支漁光曲。(《扁舟,劃出的漁歌》)”。那么,舊時(shí)的余韻翻唱著今天的吳歌,猶如水中的清凈性靈抵達(dá)著質(zhì)樸的心空,促使濡濕的光陰流動著漕河、苦河與靈河的氣韻。你想:“入夜。漁火。水天一色的朦朧中倒影著燈火點(diǎn)點(diǎn)…閃爍的魚燈,點(diǎn)亮一水朦朧(《魚燈,點(diǎn)亮的朦朧》)”這樣月朦朧,情朦朧的思維幻覺,比興幽深,事理雙切,就會不時(shí)地把我們領(lǐng)入了詩中之詩的幽雅心境;或者重溫張繼筆下的的風(fēng)雅情懷,爽朗湍激,纏綿悠揚(yáng),從高亢嘹亮的婉轉(zhuǎn)中,激昂一片蓮心與吳歌的比目漣漪;然然地,把我們帶進(jìn)經(jīng)蘇州的風(fēng)水八面上,目視座座古橋,搭建一泓古今化禪的交響思潮;不經(jīng)意流動的心靈醉入京杭大運(yùn)河里,游弋著隋煬帝時(shí)代所修建的河流;同時(shí),也佐證著這座古老城市的底蘊(yùn)。事實(shí)上,詩人創(chuàng)作是沿襲著以“歌為教”的吳儂軟語,吹奏著悠揚(yáng)的笛聲:“亭臺前練功的大叔一招一式都帶著古風(fēng);水榭里炫音簫管飄出昆曲、評彈的古樸幽雅” (《覓渡橋》)。然而,站在今天的街巷與縱橫橋上的交匯,撫今追昔,不僅縈繞著古城的橋、街、巷、弄的古色雅氣,憂慮著文人騷客對蘇州抹不去的記憶。無論是數(shù)不勝數(shù)的巷子弄堂,還是巷佰之間文物遺跡,五花八門的地名背后,都寄寓著因果宿緣的淵源。如,黃鸝坊橋,古代這里曾是黃鸝市場,一個(gè)個(gè)婉轉(zhuǎn)的聲音,猶如一只只儂軟的黃鶯,在橋上回旋吳歌的咿呀南音。于是,詩人筆下的《黃鸝坊橋》:“橋堍,蹬三輪車的大叔,聽著收音機(jī)里的家鄉(xiāng)小調(diào),白天看橋頭,夜晚看丫頭。”烏鵲橋,與闔閭城同建,位于“子城”正門前直街上,建城之初,此處有吳王烏鵲館,橋因館得名。又好比詩人筆底的《烏鵲橋》:“賣菱藕的小舟咿咿呀呀搖過橋洞,攪醒了一河星星,船娘的江南小調(diào)點(diǎn)亮了枕河人家……”是啊,大街小巷都演義著尋常巷陌的故事,“攪醒”的意切,“點(diǎn)亮”的情深,又怎能不讓詩人去思考先哲播德的人文常懷呢?

韓111.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2)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4-27 18:45 上傳
(韓樹俊長篇報(bào)告文學(xué)即將出版)
“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 唐寶歷元年(825)年初,被任命為蘇州刺史的白居易,面對一處處曲折蜿蜒的綠水,縱橫交織著東西南北的河道,吟唱的詩句使各色小橋的奇姿異態(tài),更覺波光粼粼;不禁地由衷地感嘆這商賈云集之地,城外稻香魚肥的臥野,城內(nèi)萬艫充塞的河道,宛如蘇繡,蘇扇、香山幫等藝術(shù)的化向,順從地流進(jìn)流出,盈盈地,浸潤著蘇州人的氣質(zhì)體韻。柔吧?不柔!水的里里外外如同吳姬的品格,折射出人類精神不變的衿情,回望著審美規(guī)則在任何時(shí)代都具有一致性的自我觀照。如《萬年橋》“霓虹燈將大運(yùn)河水照得格外迷人,一艘艘滿載客人的游船,也載著評彈和昆曲的腔調(diào);我卻想聽賣魚娘娘的吆喝,賣花姑娘的清唱……” 毋庸置議,作者在追隨著歷史的足跡中,一個(gè)“想聽”的意念蠕動,卻把吳地盤歌的原始芳香,一層一藏地,剝落昔日滄桑的斜陽,潛意識地獵射著虎丘塔的雕像,無為地沉思在水一方的性情交融。如《蟠龍橋》:“兩岸的仿古宮燈將古運(yùn)河水照得波光粼粼,三孔蟠龍橋的倒影是流水中古箏曲的悠悠音波……”為此,詩人律動的隱情,昂然地借用“照”字的飲水思源,把滿城的舞榭歌臺和園林勝跡,化著一泓泓漕水的溫馨,滋潤著生我養(yǎng)我的水土,為姑蘇名人的故居,縫聯(lián)著文化的深處,靜靜地,走近蘇州人的純樸厚德之中。像《青石弄5號》:“一位永垂不朽的教育家葉圣老”, 畢現(xiàn)出一個(gè)從事編輯和教學(xué)工作者,“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形象。像《王長河頭3號》:“古城一座私家花園,那里的主人珍藏的貴賓簽名本上,均有共和國的總理等來自五洲四海的外國朋友”。蘊(yùn)藉著土地的仁義淳德,所閃耀著質(zhì)樸的思想光環(huán)。還有《廟堂巷16號》:“前門傳來賣菱藕的農(nóng)婦軟糯的叫賣,后門響起嘟嘟嘟,賣糖粥的竹杠聲,巷東頭有養(yǎng)育巷里黃包車的叭卟叮當(dāng),巷西頭有剪金橋巷賣花姑娘送來的花香”。 一個(gè)個(gè)香草美人,喃喃而歌,用甜軟的懇切歌喉;踩曲著吳歌的音符,酥潤著我和我們的浮躁心靈,仿佛是一串串的傳統(tǒng)性情所折射的真實(shí)摯愛,回放剎那間的人性之美,人人都需要呵護(hù)、慰籍和支撐的情感關(guān)照。然而,卻從《百步街12號》里感受的嘆息:“殘?jiān)0甙唏g駁破敗的墻。風(fēng)雨中,曾經(jīng)的溫馨小樓,面臨著一個(gè)血淋淋的‘拆’字。”那么,一手一斥,一字一痕,任一個(gè)‘拆’字的換位心空,都將攪拌著自我私下的嘀咕,本體“一”被弄開、分散和毀掉的得失。假如是一種占卜方法,自然沒有越王余算的滄海桑田;然而,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吳王夫差,攜愛妃西施漫步的小巷,頃刻之際的惋惜,天空藍(lán)得像粘稠的愛情,伸縮的距離失落了脆性的馳騁,一張一馳,一松一緊,那么,‘拆’的辯證對立統(tǒng)一,又漸漸地沁入一腔拾得的心田,緩緩地縈回三吳的歌聲世界。無論是街頭那甜膩膩的吳娥姿態(tài),還是香噴噴的吳羹菜肴;也不管是刺繡抖落的慧心巧手,還是彈詞盤旋的吳歌場景;那吳根越角的縮影,都將永遠(yuǎn)沉甸甸地思索著潛龍勿用的歷史殘香之中。為你解讀,吳歌的曲調(diào)音符以纏綿哀怨的聲音而傳世,吳地的莼羹鱸膾以越相越吟的美味而著稱。 “石頭匯成的瑪尼堆……來自天上的圣水/化成大地母親甘甜的乳汁/靈性之水/吉祥甘南心靈的腳步,悠長的命脈”,讀著思著詩人語言悖謬于日常生活的自然語言,如同從《吉祥甘南心靈腳步》的筆端,進(jìn)入《劃過天空的流星》一般,一字一詞的外來文化,優(yōu)雅地從高亢嘹亮的婉轉(zhuǎn)中,借助自我地域文化的融合,激昂一片情感蓮心的波紋。你看,那《勒尤,布依人愛情的見證》:“尋找情人的小嗩吶”。 一碗布依人的攔路酒,一舀蘇州人的忘情水,使性情中人的性格和真情的實(shí)感,裹成一個(gè)蠶蛹鞭影的警示。那么,一切平等的生命之初,設(shè)想人與動物不了之情,觸動著某個(gè)暖心的瞬間,自然會感應(yīng)著靈性動物的遠(yuǎn)古,在沒有道德文化的制約中,人與動物的親近與和諧,人倫之間的接觸與中庸,如同詩家所說的大地母親,讓一切甘甜的乳汁成為靈性之水,悠長著心靈的腳步和性情的命脈,渾然一體而沒有彼此。因此,人生最大的兩件事情,在生與死的文明交匯中,詩人用自我的體會走進(jìn)紅山文化,天問著《人獸同葬》》:“生,共存活;死,同長眠。天下是飛禽、走獸、游魚、先民的天下。”也由此人性獸性的傳遞,生命的夜晚像蠟一樣軟,或者性情的整個(gè)時(shí)刻靜得異常一樣的硬;其陰陽的合一和對壘,驅(qū)使古往今來的反思,性內(nèi)情外的觀照,染起我們回顧詩人傳遞地方文化的精神指向里,作畫度曲也罷,吟詩創(chuàng)新也罷,必然要在天道、地道、人道的向度里,找準(zhǔn)自我的維度。所謂的效法天道盈而不溢,遵從地道量體裁衣,藏行人道崇尚謙卑。故此,不管是多么有才氣的詩人,自我要有一顆價(jià)值觀的胸懷,超我要有一種人生觀的適合,本我才有宇宙觀的浮根;其三魂的詩性才會靈動七魄的詩情,延續(xù)不絕地取之天、地、人的精華;然后,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基點(diǎn),從柔中寓剛的柔道取美,有機(jī)地接納西方的剛耿義心,互相提攜,在性浮情沉的自我觀照里,捻著生命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洞見拈花一笑的靈魂。 散文詩是一種藝術(shù)的新型門類,其誕生的源頭除了十九世紀(jì)中葉時(shí)期,歐洲浪漫主義運(yùn)動的產(chǎn)物之外;然而,早在先秦(公元前21世紀(jì)--公元前221年)時(shí)代,莊子《南華經(jīng)》中的許多片斷,屈原的《漁父》就隱隱約約地聞到到散文詩的芳香,凸顯出“楚辭”抒情的浪漫氣息;其思維方式均是沿著“辭賦””的脈絡(luò)河流,反饋中國本土集體文化的遺風(fēng)。那么,借如詩家的筆調(diào):“斑斑銹跡是你劃過歷史天空的印痕/霍霍劍鋒是你成就余眛王權(quán)的象征”(《吳王余眛劍》)。試想,春秋晚期的“吳越第一劍”,起源于戰(zhàn)國時(shí)代的“辭賦”,其首尾銜接的某種靈源,在詩人親切愛憐的疊音對接下,窺見著姑蘇月色的閉影。由此,當(dāng)我們從風(fēng)俗、宗教與神學(xué)的遐想中,以仁德的詩學(xué)象征體系,尋找自我筆桿的性心代言,靈顯詩道的恒變。故此,在信仰、焦慮和守信的傳統(tǒng)價(jià)值觀照中,學(xué)習(xí)韓樹俊先生善于從司空見慣的物質(zhì)形狀,變成道德文化的藝術(shù)心象;邇后,通過屬于文字的意識符號,連接著水鄉(xiāng)本地土壤的潛意識,輻射著自我個(gè)性的思想之道,揉合成一首首吳歌風(fēng)骨的美學(xué)花雕。 從審美的觀道來看,筆下意象的悟性連接,一定要善于通過隱喻、象征和高度的概括力,把看似無關(guān)聯(lián)的片斷,簡練而異常豐富地表現(xiàn)出來,拿捏成一束花的憨笑。毫無疑問,詩人是我們橫向?qū)徝赖南驅(qū)ВM管《風(fēng)潤姑蘇》在詩情的縱向表達(dá)上,不盡詩性本體的初衷,缺乏對一事一物的哲學(xué)思考和深入淺出的暗香回環(huán)。但是,在生命的長河里,這種本性的純善至美,交叉運(yùn)行著中外對立的性情視野,在時(shí)間涌動的波濤中,推動著最自由最充沛的身心自我,如同晉朝詩人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nèi)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從而使山水虛靈的禪化,返照人性自我的情致化性,有意無意地,把虛、實(shí)、有、無的藝術(shù)構(gòu)成原理,轉(zhuǎn)化成當(dāng)代散文詩人的啟示、覺醒和迭變,也呼喚著未來散文詩觀的獨(dú)語走向和藝術(shù)審美的演繹辨認(rèn)。 2017年3月23-28日萬年青云

東北王彭林家.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2)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20-4-24 18:01 上傳
作者簡介:彭林家, 哲學(xué)家,著名評論家,聾龍?zhí)焐厴I(yè)于東北師大中文系。中國散文詩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散文詩作家聯(lián)盟評論委員會主任,中國詩歌在線吉林、國際頻道詩評編審,國家一級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中國蕭軍研究會主辦的《原創(chuàng)文學(xué)界》副主編,中國微型詩\《0度詩刊》顧問,中國針刀醫(yī)學(xué)副秘書長,全球漢詩總會聯(lián)絡(luò)主任,北京倉央嘉措國際詩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新詩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詩人,廣東凈土生態(tài)旅游有限公司文化總監(jiān)。 《詩歌周刊》提名批評家,2017、2018年中國詩壇實(shí)力詩人,入《2019年中國年度優(yōu)秀詩歌選》。為全國各地的作家、教授、小說家寫序、寫評論1000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裂開青云的紅冰》等,作品散見于《詩刊》《星星詩刊》《詞刊》《散文》《意文》《散文詩》《人民日報(bào)》《印尼日報(bào)》《中華詩詞》《中國詩詞年選》《寰球詩聲》《詩詞世界》《陜西詩詞》《江西詩詞》《江西文史》《中國文學(xué)》《中國詩界》《中國之聲》《江西詩歌年選》《中國詩歌年選》《中國百年新詩經(jīng)》《中國散文詩年選》《中國新銳華語詩歌經(jīng)典》《世界華文散文詩年選》《世界華文文學(xué)研究》《語言與文化研究》等100多種國內(nèi)外報(bào)刊,任多家媒體的顧問、主編和編委。曾獲全國詩詞、辭賦、詩歌、散文、散文詩、小說評論征文及其他文體一二三等獎。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