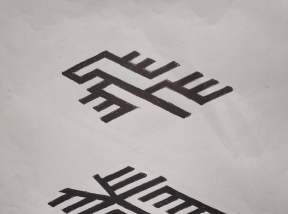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南島(青衣童生 于 2019-1-6 11:30 編輯
南島新漢詩19首
舊報紙 國事 不知誰早已撕掉了 糧食和蔬菜 被過冬的螞蟻搬走了
一個乞丐撿起 揉作一團 一腳踢得老遠老遠 像是要踢走上面的壞天氣
賣烤紅薯的大爺
不餓 也稱一斤 給七塊錢 給他添人氣 給他當陌生的兒子
此刻 風也不吹 停在對岸 嗅著紅薯香味
看他臉上 白花花的雪 比來時 下小了點 輕了點
秋風
不知打哪兒來 站在面包店的櫥窗外 看了一眼沒有進去 隨手扯下路邊一則招工廣告 并借理發店門前的落地窗 打量了一下自已 然后 踉踉蹌蹌 拐進一條胡同里
山稔熟了
落葉 像向晚的鐘聲 遺下的時光碎片 一枚 黃昏里 追逐著 另一枚
我挑著一擔山稔 逆風而行 有人喊:來一斤
他吐出的鄉音 加重了秤坨的份量
落葉 一枚 晚風里 追逐著 另一枚 不知是它們 驚擾了這里的秩序 還是迎面趕來的 兩騎翩翩 打破了整條街的寂靜
只覺得 肩頭的擔子 更沉了 若不是山稔 有人買走一些 若不是 被剛寫完的一首詩 ——扶住 ……
三輪車夫 奔馳在胸前的空曠里 呼呼的風聲 如刀 睫毛間的霜露 如刀 醉客雷霆的鼻鼾 如刀 三更夜的指針 如刀
而你 你更像一把刀 深深地 將未央街 割疼了
在小攤
此刻 黃昏烤熟了半只雞 剛好下酒 起風了 剛好與路邊的椿樹劃拳 燈火涌來 像故鄉荔枝溪潮漲 漫過杯里的自己 剛好 被爬上來的月亮 銜住
回到工棚
已沒一點力氣 剛好 下雨了 飲幾口 剩余的 替我落淚 走不動了 剛好 手背上 一只趕路的螞蟻 分擔一段旅程 風吹過的胸膛 剛好清明 麥子瘋長 娘的墳間 雜草瘋長
城鎮化 莊稼 河流 炊煙走了 這里的人也走了
只有西邊 那頭落單的老黃牛 對著落日 舔了又舔 不忍下山
民工
腳手架上啃著一塊 又冷又硬的大面包
那些散落的碎屑 是無法下咽的鄉愁
起風了 落葉 這時光的碎片 撒在心口 像鹽 腳手架 不禁晃了晃
電線桿上的小鳥 你若有情 請替我飛回故鄉 問一問爹娘
看晚報的男人
起風了 來不及讀 掉下來的幾片暮色 加劇了頭版時局的動蕩 而躲在熱咖啡里看報的 那張四十歲臉龐頓時 蕭蕭落木
不敢久留 他豎起衣領壓低帽沿 攜帶秋色 再次 混進夾縫的蟻群里
長椅上
一些人走過 一些葉子便掉下來
一小片風 像馬車 將我 拉成遠方
一只鳥的來訪讓空椅子 又少了幾分人間
冬的夜街
魚群來來往往 用彼此的異鄉 相互取著暖 有的累了 游進站臺 呵出一圈圈炊煙 努力蓋住 廣告牌上的紅唇 有的喝多了 在路邊 吐出故鄉 有的變瘋了 像一個破洞 成為這條大街無法治愈的疤痕 ……
我剛剛擠出魚群 被趕來的一陣風 肆無忌憚地搜身
青春祭
還有什么想說的 西風瘦 落日 秋天一樣老黃
還有什么想說的 額頭的河流 又急又深 早已淌不過去
還有什么想說的 翻手 不是雨 覆手 也不是云
還有什么想說的 冬天 還是那么專 制
想說的 不想說的 一場雨后 都在眼眸里 化為藍色的余煙
你不來,我空著
檐滴 在石階上 將流水彈空 落花彈空 長椅上的落葉彈空 深深淺淺的腳印彈空
你不來 我漸漸被季節 彈成一首空白的詩
晨報 晨報上 有風 小販挑著擔 在夾縫里穿行 身體還殘留一半的夜色 邊角處的乞丐 還沒接到第一單生意 圖片的長椅上 一對老人 在談論早間落的第一片秋葉 公文包 大腹便便 將專欄的馬路 又擠寬了一些 政客在頭版 游說著他的臣民
遲來的陽光 在亂堆廣告中 總算替我 找到一則招工啟事
月,又圓了
淚水在集結 漫過我原野一樣 荒蕪的臉 燒出的小路 長滿坑 一聲聲蟲鳴 風一樣冗長 牽出我薄薄的影
而母親 此刻一定站成 村口那棵老槐 提著月亮
老家很小 老家很小 村口的風一吹 院里的老槐顫抖不停 地邊的草一埋 看不見了彎彎小路 老家真的很小 腳一伸 到了外省
個人簡歷:原名:蘇興龍 ,筆名:南島或青衣童生,男,大專文化,生于海南島,現居海口。作品散見于《中國詩歌》《詩潮》《椰城》《湛江文學》《詩歌月刊》《西部作家》《山東文學》等。 詩觀:1、詩就像魚竿,在寺廟釣木魚。2、詩是人類認識自己的一個過程。

2018年7月在浙江嘉興南湖 (1).jpg (270.45 KB, 下載次數: 9)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19-1-6 11:30 上傳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播
轉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

 那喝杯熱開水吧
那喝杯熱開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