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靜川 于 2021-5-12 07:40 編輯
詩歌理想的旗幟與故土
——淺談詩人石艷的詩
靜 川
石艷在吉林詩人中,是一位身上頗多詩人氣象的人。無論她在部隊服役時,還是退役在單位任領(lǐng)導(dǎo)職務(wù)期間,到退休后擔(dān)任雪柳詩社副社長,石艷總是最有“詩人緣”的人;她善待同行同事,甚至親近晚輩后學(xué)的品行,總是被人津津樂道。我敬重她的理由有二,一是她充實、豁達、內(nèi)在的生活態(tài)度和藝術(shù)追求的一以貫之;二是她平易、樸素、親和、本色的詩歌理想與詩歌實踐的有機結(jié)合。 著名作家林語堂先生說過:詩歌教會了中國人一種生活觀念,通過諺語和詩歌深切地滲入社會,給予他們一種悲天憫人的意識,使他們對大自然寄予無限的深情,并用一種藝術(shù)的眼光來看待人生。詩歌通過對大自然的感情,醫(yī)治了人們心靈的創(chuàng)痛;詩歌通過享受簡樸生活的教育,為中國文明保持了圣潔的理想。在這個意義上,應(yīng)該把詩歌稱作中國人的宗教。 詩歌,曾經(jīng)是中國人的思想指南和旗幟。中國人歷來把詩歌視為一種智慧的象征,詩歌填充著我們心靈中時常荒蕪的空間,詩歌傳達著生活經(jīng)驗中往往只能意會的部分和審美發(fā)現(xiàn)。石艷多年的筆墨生涯,創(chuàng)作豐碩,我讀過她很多舊體詩和現(xiàn)代詩,有現(xiàn)場感和意境美。 前幾日我在《江城日報》“松花湖”副刊讀了幾首她的小詩,發(fā)現(xiàn)石艷對生活的理解已在經(jīng)意或不經(jīng)意間有所新的悟感。她在《故鄉(xiāng)云記》里寫道:“我身體里/長出一朵朵云/漸漸蔓延//我看到了,?老母親/長出了彎曲的/那片黑白”。 詩人的人生感悟,來自原汁原味的生活智慧的提純,并且,很含蓄。但與其說石艷徹悟生活的本身,莫如說她更深刻地洞察時代與時光不可弄丟的精義,還有每一個人步入暮年之旅的那份喜歡回顧的過程,以及草根文化與詩歌之間,發(fā)生著怎樣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她在另一首詩中寫到:“你已經(jīng)離開村莊/很久很久/村頭那棵老槐/更禿了/書童,還會端來一碗水嗎/那個傳說還在,那些根?還在/方向,有些零亂”( 那年模樣)這些鄉(xiāng)土味很濃的詩,隱喻很深的懷舊感。詩很短,但意象很多,老槐更禿了,書童,一碗水,根,和詩人的心情,零亂結(jié)尾非常耐人尋味的。 石艷創(chuàng)作與抒情的主體,大多是謳歌故土的詩篇。詩人眷戀故土,正如陽光眷戀山川、河流與大地。一個詩人的情思總是先從故土萌芽,從故土起飛;但無論他的飛翔多么遼遠,她的根都會深深地扎進故鄉(xiāng)的土地,她的詩情也終將回歸自己的故鄉(xiāng)。大詩人普希金、海涅、聶魯達、泰戈爾、艾青等無一不是故土的忠實歌者。 蘇珊.朗格說:“純粹的自我表現(xiàn)并不需要藝術(shù)形式”。故土情結(jié)永遠是詩人的心靈模式或形式,是詩人心律意緒的特定或特指,形式的力量有時候會強烈地反芻內(nèi)容,甚至超越內(nèi)容。在故鄉(xiāng)的沃土之上,誰又能分辨:哪首詩是根,哪首詩是枝椏,哪首詩是葉和花呢? 石艷的詩著意于現(xiàn)場和內(nèi)心的觸動,并且不直意去描述,“樹林的那頭,長出故鄉(xiāng)的村頭”(《晨間曲》)這是石艷詩歌的意象提示。正是憑著內(nèi)心如此的豐富飽滿的自由度,和對詩賦予的生命感,石艷的詩歌,才可以從“唯心”出發(fā),最終歸于“唯心”,才不會僅僅滿足膠著日常的用語。譬如“長出”一詞。 石艷詩歌色調(diào)濃郁,自由浪漫,詩情飛揚起來,自會神采動人。譬如《效應(yīng)》“老家的筆有點沉/速寫一畝三分/那些汗水開墾的荒蕪/是否能長出飽滿/想必一定與下筆輕重有關(guān)”;譬如:《趕山》這首詩,率性而溫情“如今 住在大山里/那些趕山人/是否又做回山的子民/山頭有炊煙升起/穿過古老的井/我無法給出準確答案/只有故土撲個滿懷”詩人沉浸在安然中,對故鄉(xiāng)的情感,似乎已經(jīng)有象無形了。還有《晨間曲》都有詩者唯心唯識的詩人情致:“清晨,穿過一片樹林/漸次掠過射來的光影/聽鳥疏密有度地說著一段故事/故事里有簡單和幸福//遠離了街市的喧囂/趟一溜兒矮草/捋一下伸展的枝葉/一股樸實的味道飄來/樹林的那頭/長出故鄉(xiāng)的村頭”寫詩是一種極好的心靈“美容”術(shù),也不排除其它功效。因為,從心靈深處射出的光彩,會照亮“天空賦予女人最奢華的經(jīng)卷”。就像她的筆名馨雨,讓人感到詩意。 石艷的詩,總感覺詩人對人生和對詩歌的那種無法抑制的激情,總感到在她的作品中,潛流或奔涌著永不止息的詩歌的源泉。是什么樣的源泉和動力,讓她在詩歌的領(lǐng)地輕盈、曼妙、忘情地吟唱?據(jù)詩人自稱,寫作詩歌其實只有幾年功夫,但是,創(chuàng)作出來的詩歌作品,卻如漫天繁星,耀眼奪目,星光熠熠。想必,在寫作詩歌之前,她必是一個與詩歌前世有緣、今生相逢的詩的寵兒,也必是一個蘊集情愛、驀然釋放的詩歌精靈。她的詩進步很快,這幾年,地市、省報、詩詞月刊,都有她的詩不斷出現(xiàn)。前一段日《北方公安文學(xué)》也收錄她一首組詩《流淌的日子》,寫的也非常靈動,新意。 艾略特說:“就感知而言,廣泛深入的閱讀并非僅僅意味著更加廣闊的天地。在一個真正具有欣賞能力的心靈中,感覺并非是隨意堆積起來的,而是自身形成的一個結(jié)構(gòu)。”石艷女士的詩歌,充滿了微妙的聯(lián)想,其意象結(jié)構(gòu)涉指方向非常廣闊,邏輯縝密,令人思路大開而不迷茫。詩人內(nèi)心的色彩是常人難以識別的。 石艷,不僅僅現(xiàn)代詩寫的不錯,她的舊體詩寫的更意境。前幾天我在微信平臺讀過她的《五絕.詠荷》,讓我想起了晚唐詩人李商隱的《贈荷花》,他們的詩,美,都著重于葉,讓我感到有些新奇。 寫詩,無論是舊體詩抑或現(xiàn)代詩,一定要有深刻的思想內(nèi)容才是好詩。民間一直流傳著一句諺語,說“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石艷女士的這首五言絕句,形象地表現(xiàn)了和這句諺語相似的可貴的新思維。李商隱的《贈荷花》說的是大多數(shù)人總是重視花,不重視葉。花栽在盆子里,葉子卻讓它落地成為塵土。但荷花的紅花綠葉,卻配合得很好,它們長期互相映照、互望、互襯,荷花荷葉共伴凄美,一直到綠葉衰老,紅花凋零,使人悵然。 石艷的《五絕.詠荷》,也是思之于葉,反襯于花,意在于境。“熏風(fēng)搖碧傘,十里玉婆娑。”形象,詩的語言有動態(tài)美。詩人用一“搖”字,讓文本的畫面隨風(fēng)而動。“碧傘”一詞有色澤也有質(zhì)地,不僅形象,也給下一句的“十里玉婆娑”,做好了有效的鋪墊,同時也突出了,蓮葉給人的視覺,帶來強烈的沖擊力。無邊無際蓮葉,仿佛與天宇相連,氣象宏大,既寫出蓮葉在熏風(fēng)中漫舞的樣子,又渲染了天地之壯闊,具有極其豐富的空間造型感。石艷的這兩首詩雖然是詠荷,但她始終沒有提到荷花,我覺得此時的作者就如一朵蓮花,影印在詩里,她與荷葉盤旋舞動的情形,讓這首詩又多了一層隱喻。 寫詩,確實要有好的思維和感受,意境不需要刻意去營造,也會隨之而來。石艷寫詩,我覺得她很智慧,第三句她用自贊的方式轉(zhuǎn)筆,“偶得娉婷句,應(yīng)為點棹歌。”,一下子就把這首詩最后的收筆,貌似不經(jīng)意卻是精華了這首詩的詩眼。尾句妙在一個“棹”字,讓讀者眼前的荷塘,合理地劃入一葉小舟。一首詩能如此詩畫有緣,和作者一起聆聽棹碰船來的水聲。 石艷愛好廣泛,除去喜歡舊體詩和現(xiàn)代詩,她還喜歡歌詞創(chuàng)作,她創(chuàng)作的歌詞《朵朵軍花綻芳華》被我市作曲家趙鐵橋先生譜曲,我在網(wǎng)絡(luò)上聽到齊子萱的演唱,很有軍歌的感染力。總之,詩人的胸懷有多大,她詩歌的領(lǐng)土,就有多廣闊。
(作者簡介:于江龍,筆名靜川,中國詩歌學(xué)會會員,魯迅文學(xué)院92屆文學(xué)新人創(chuàng)作研習(xí)班學(xué)員,《詩選刊》第三屆高研班學(xué)員,吉林省作協(xié)會員,吉林市作協(xié)副秘書長,吉林市詩詞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昌邑區(qū)作協(xié)主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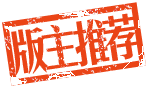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