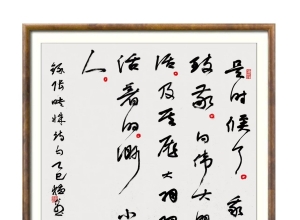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彭林家 于 2019-10-5 15:10 編輯

佛心創(chuàng)作儒道說
論談詩歌審美的難度和逆向思維的初心反芻
彭林家
詩歌是語言情感的載體,借助外界的物象,追尋天地萬物之始,獲得一種引人奮進(jìn)的質(zhì)地而表述最初的本心,謂之初心太極。太極者,太始太古之初,極者一也。物物都有太極,太極本無極,故曰太虛。月暈而風(fēng)﹐礎(chǔ)潤(rùn)而雨,如同詩人虛無縹緲的幻想境界。譬如,新詩就是從胡適的一對(duì)蝴蝶而開始,思維心法中,乃古典詩詞的散文化,好比辭賦演變成現(xiàn)代的散文詩。其自由詩性的演繹,可表現(xiàn)于南北朝的庾信《怨歌行》:“家住金陵縣前,嫁得長(zhǎng)安少年。回頭望鄉(xiāng)淚落,不知何處天邊。”顯然,這種六言自由體的白話詩,語言直白,敘事精確,即為南朝宋的鮑照,在漢魏六朝樂府詩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歌行體,不講究平仄,字?jǐn)?shù)五七言為主,參差不齊,篇幅可長(zhǎng)可短可變韻,亦稱古詩、古風(fēng)。時(shí)稱:南照北信。 《莊子·天下》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那么,傳統(tǒng)詩與現(xiàn)代詩,在心法共振與異別上而言: 一則,古詩者,從外到內(nèi),側(cè)重集體潛意識(shí),將空間上的延伸構(gòu)成橫向思維;爾后,以象生意形成意象,讓其渾象的太極整體之性,帶動(dòng)陰陽物象的局部之情,使其意象銜接的上聯(lián)、下聯(lián),互生互藏,互靜互動(dòng),即為主體為詩性,副體為詩情。哲學(xué)上,世界的本源是運(yùn)動(dòng)著的物質(zhì),即為“物質(zhì)第一性,意識(shí)第二性”,乃客觀唯物主義。然而,世界是上帝神靈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我心在我心,神靈決定任何事物,世界的本源是意識(shí),乃客觀唯心主義。二則,新詩者,從內(nèi)到外,強(qiáng)調(diào)個(gè)人潛意識(shí),將時(shí)間上的推移構(gòu)成縱向思維;爾后,以意生象形成意境,讓意象的陰陽局部之情,波動(dòng)意境的太極整體性,使其上下結(jié)構(gòu)而外呼內(nèi)喚,內(nèi)靜外動(dòng);即為主體為詩情,副體為詩性。哲學(xué)上,世界的本源是永恒不變的物質(zhì),卻否定了事物是運(yùn)動(dòng)的,乃主觀唯物主義;然而,世界的本源是意識(shí),我思故我在,萬物取決于人的內(nèi)心,乃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diǎn)。三者,比較之,無論是古詩還是新詩,語境的時(shí)空差均是內(nèi)詩外歌的顯象,從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表達(dá)著人心如何回歸道心的啟示,孕育著上天五行投影于人體五臟的精神運(yùn)動(dòng)。詩者,詩以道志。詩是意向,意也,脾藏意,后天之本,心腎媒介,真意真土,為左腦意識(shí)的第二思維。需要修行,將情欲克制而返回第一思維。歌者,聽歌識(shí)音,歌是聲音,來源于肺的七魄七情,反射三魂三性之肝,仁木德象,象也;心藏象,先天之本,心火腎水,水火既濟(jì),為右腦潛意識(shí)的第一思維。如腦波誘導(dǎo)及潛意識(shí)音樂,像夜鶯一樣的天然籟音,將直接引發(fā)右腦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 哲理上,主觀唯物主義和客觀主義,都肯定了物質(zhì)決定意識(shí),區(qū)別在于是否看到物質(zhì)的運(yùn)動(dòng)屬性。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相同點(diǎn)在于肯定意識(shí)決定物質(zhì),分歧點(diǎn)在于誰的意識(shí)是第一性。由是等同于美學(xué)的觀點(diǎn):陰與陽、雞與蛋、運(yùn)動(dòng)與靜止、物質(zhì)的潛意識(shí)與精神的意識(shí),則如何看期初的起點(diǎn)角度。就詩歌而言,就是一種不同角度的互換性。比如,詩人之心,心生相,為物相的存在狀態(tài),當(dāng)?shù)搅四骋慌R界點(diǎn)的時(shí)刻,物相變成物象, 其文藝作品所創(chuàng)造的典型形象——儒家的圣象,也就是物體形象的景物風(fēng)景——道家的天象,太極一也。 谷神隱土德生味,麥穗飄云道悟香。無疑,新詩從舊體詩脫胎而來,語境的差異,也都是根據(jù)時(shí)代的需求而生成的語言平臺(tái),映現(xiàn)出螺旋形上升的一波三折。原理上,佛心是連接人與神的橋梁,道心是仙界,儒心是人杰。三者之間的能量合一,元龍者也,即為道教對(duì)"得道"的別稱——元龍。詩人抒發(fā)壯懷的登臨處,元龍百尺樓,仿佛陳子昂《登幽州臺(tái)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dú)愴然而涕下!”如是氣節(jié)之士的作品——谷音,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山谷,意謂空虛。谷神:指由道質(zhì)和道性所構(gòu)成的大道,也可謂大自然。猶如自然的磁化力,在逆向思維的反芻上,其思維遷移如劉備所說:“若元龍(三國(guó).陳登)文武膽志,當(dāng)求之于古耳,造次難得比也。”古往今來,沒有誰比得上這樣愛國(guó)的情懷。因此,詩歌至美也莫過于如此介入與思索;所以,無論是村莊、林場(chǎng)、民工,稻田,甚至一只鳥,一朵花,一棵樹,一只老虎和猴子,真情意滿;用詩歌觸摸了人在生活中的疼痛感,將詩人的悲憫之心,化成一種抹不掉的“身份”密碼,堅(jiān)韌凸顯詩歌的生死現(xiàn)場(chǎng)。正是詩人初心的道德馳懷,《華嚴(yán)經(jīng)》里則說:“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初心是出生時(shí)的第一聲啼哭,人與森林、人與動(dòng)物的矛盾、沖突、融合的世界,融合成一縷縷人生經(jīng)歷挫折,猶如戀愛時(shí)的第一次萌動(dòng);那真確如斬,痛癢切膚,呈現(xiàn)出淋漓豐沛的生命情態(tài)生花成最初生活的辛苦,則是夢(mèng)想時(shí)的第一次出發(fā),更是在人生的起點(diǎn)所許下的夢(mèng)想;心甘情愿詩意的記錄,抑或以詩歌敘事的方式,以一個(gè)個(gè)趣味盎然或觸目驚心的故事和細(xì)節(jié),記錄一生的自愿,將渴望抵達(dá)的目標(biāo),精致的描述,不作隱喻,不忘記最初為什么開始,象征一類的經(jīng)營(yíng)就是力量。納蘭性德說:“人生若只如初見。”初心遺忘,走得十分茫然,多了許多柴米油鹽的奔波,少了許多仰望星空的浪漫。納蘭性德說又說:“卻道故人心易變。”一個(gè)“變”字,五行里謂之金,前面一個(gè)“初”字,五行里謂之木。金不克木謂其不隔情,仙界的逆向思維;反之,隔情,乃人界的正向思維,后天八卦中的復(fù)卦。情是喜怒哀樂的情感表現(xiàn)或心理活動(dòng),《中庸》里的“喜、怒、哀、樂”的情感點(diǎn)上兒,將至而未至,其活動(dòng)的愛、惡心理而產(chǎn)生“懼”恐則氣下,是指恐懼過度,可使腎氣不固,氣泄于下,臨床可見二便失禁;或恐懼不解則傷精,發(fā)生骨酸痿厥,遺精等癥,均是一種自我情感的貪婪,而造成心愿底氣不足的表現(xiàn)而已。 類似于顧城的《世界和我》:“開門帶上最合法的表情,不要看見別人也藏好自己的心。”一個(gè)“藏”字的的本性點(diǎn),反襯“合法”的情感點(diǎn),契合著現(xiàn)代人“逢人只說三句話”的防備心理,但要使世界感到愉快。必須讓微笑永遠(yuǎn)凝固在嘴邊。 正如紀(jì)伯倫《先知》所說:“不要因?yàn)樽叩锰h(yuǎn)而忘記為什么出發(fā)”。太遠(yuǎn)者,就是七情的節(jié)制,失去了三性的控制力。七情者,是詩人心理或生理活動(dòng)的七種感情,或情緒波動(dòng)弗學(xué)而能也,卻其說不一。 一曰:儒家《禮記·禮運(yùn)》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則是強(qiáng)調(diào)外界六欲的感覺。《孟子·告子上》里的“性善說”,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種子,七情也就是人的“本心”。肝為心之體,肝藏三魂,謂之三性(善性﹑惡性和無記性)是人性的三個(gè)來源。如東漢建安七子劉楨的詩《贈(zèng)從弟·其二》:“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fēng)。風(fēng)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詩人運(yùn)筆搖曳多姿、富于變化,贊松柏,則辭氣壯盛、筆力遒勁,正可與它的抗風(fēng)傲霜之節(jié)并驅(qū)。其中,“風(fēng)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繼承了孔子的"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思想,越是風(fēng)聲凄慘,越是要挺立風(fēng)中。其堅(jiān)韌不拔的品質(zhì)如“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本性(三性)者,比德(七情)也;用自然界的事物來比喻人的道德境界,堅(jiān)貞自守,不因外力壓迫而改變本性,號(hào)召人們處于亂世的時(shí)候,如同松、竹、梅、菊三友人格追求,從而進(jìn)一步喚起人格境界的自我提升。藝術(shù)上,以象征手法,借松柏挺立風(fēng)中而不倒、歷經(jīng)嚴(yán)寒而不凋,自喻高潔、堅(jiān)貞的情懷;其翠峰插空,高云曳壁的精妙比喻,化深?yuàn)W為淺顯,化抽象為具體,化概括為形象;著筆不多,卻畫龍點(diǎn)睛,使它們個(gè)個(gè)風(fēng)骨棱然。正是詩人自身高潔之性、堅(jiān)貞之節(jié)和遠(yuǎn)大懷抱,將挺挺自持的氣骨的三性,把無情之物鑄造得高風(fēng)跨俗而富有生氣的七情,是謂本不期于詠物,而在于贈(zèng)人的儒家思想。 二曰:佛家《佛學(xué)大詞典》曰:“喜、怒、憂、懼、愛、憎、欲”,則是強(qiáng)調(diào)內(nèi)界六欲的感知。佛說六識(shí) 眼、耳、鼻、舌、身、意 ,產(chǎn)生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 ,故有七情。 肺為情之用,反射于肝魂,即為:三自性,《成唯識(shí)論》卷八,則認(rèn)為事理﹑迷悟一切諸法,均不出此三性(法相宗所主張的遍計(jì)所執(zhí)性﹑依他起性和圓成實(shí)性)。肺藏七魄,有“根輪(海底輪、純真輪) 腹輪(真知輪、生殖輪) 臍輪(正道輪) 心輪(仁愛輪) 喉輪(大同輪) 眉心輪(額輪、寬恕輪) 頂輪(自覺輪) ”七大能量場(chǎng)。如海底輪,為人體整個(gè)能量系統(tǒng)的根,所有的能量都經(jīng)由海底輪出發(fā)——本我。生存自信的——自我,若是海底輪強(qiáng)烈創(chuàng)傷的人,則沒有安全感,覺得自己的存在一文不值——超我;必須要不斷的抓取金錢、權(quán)力等等來填補(bǔ)這恐懼的空洞;或者尋求權(quán)威的指導(dǎo),如宗教、政治領(lǐng)袖的保證;亦或進(jìn)入精神領(lǐng)域,瘋狂的追尋特殊的神秘經(jīng)驗(yàn)來取得慰藉,最糟的是吸毒來麻醉自己。其創(chuàng)傷來自于胎兒受到碰撞、穿刺、嘗試墮胎,嬰兒被醫(yī)生拍打、粗暴的夾出,離開產(chǎn)道時(shí)遭遇強(qiáng)光、巨大聲響;或是母親哭喊、咒罵,與他人激烈的爭(zhēng)吵或打架等等,造成驚嚇傷害,烙印在潛意識(shí)(右腦)中造成創(chuàng)傷,影響生命自我(左腦)的態(tài)度。如瑜伽,透過對(duì)肉體的覺知,所有的意識(shí)集中在海底輪的靈蛇部位,和海底輪能量取得連結(jié),穩(wěn)定自我邊界,獲得安定感。詩人構(gòu)思,可以借助“智慧手印冥想”開啟海底輪的能量,如顧城的原始思維,《遠(yuǎn)與近》:“你,一會(huì)兒看云,一會(huì)兒看我;我覺得,你看云時(shí)很近,看我時(shí)很遠(yuǎn)。”也叫詩性思維,道生一也。 三曰:道教與中醫(yī)相同,道醫(yī)同源,《普濟(jì)方》曰:“喜、怒、憂、思、悲、恐、驚。” 七情是人體對(duì)外界客觀事物的不同反映,若是情志激動(dòng)過度,在突然、強(qiáng)烈或長(zhǎng)期性的情志刺激下,超過了正常的生理適應(yīng)活動(dòng)范圍,使臟腑氣血功能紊亂,就可能導(dǎo)致陰陽失調(diào)、氣血不周而引發(fā)各種疾病,稱為內(nèi)傷七情,分屬五臟時(shí),以喜、怒、思、悲、恐為代表,稱為"五志"。情志太過,則損傷五臟: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悲憂傷肺,恐驚傷腎,致使七情波動(dòng)而影響人的陰陽氣血平衡和運(yùn)行。比如,詩人三性(元精﹑元?dú)夂驮瘢﹦?chuàng)作,就是依賴腎來表達(dá)驚恐之志的臟器,肺是表達(dá)憂愁、悲傷情志活動(dòng)的器官。人體內(nèi),肺藏七魄,胰(胰)藏八精,焦(胃、大小腸、生殖系統(tǒng))藏九智。從一意至九智共四十五個(gè)功能點(diǎn)之能量充盈不缺,脾屬土,即地,焦為后天,人生于天地之間,必法自然,即達(dá)天人合一,磁化著大宇宙的能量,為詩人的能量的最大值。心法上,從小我到大我的推進(jìn),試讀顧城的《我是一個(gè)任性的孩子》:“我是一個(gè)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xí)慣黑暗的眼睛都習(xí)慣光明。”詩中的自我是一種一元論的“任性”狀態(tài),“擦去”與“畫滿”的筆勢(shì)宕跌,飄逸多姿,正顯現(xiàn)了“習(xí)慣”的大智若愚的灑脫身影。到了二元論的辯證上,《一代人》則說:“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黑夜”與“黑色”的疊雙,平易通俗,映襯抑揚(yáng)、著色清淡,意境上卻反襯“光明”的黑白反差,言簡(jiǎn)意明,正適宜淡泊高潔之性,大道至簡(jiǎn)。

微信圖片_20190930174522.jpg (0 Bytes, 下載次數(shù): 3)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cè)
2019-10-4 11:33 上傳
顯然,中醫(yī)學(xué)不把“欲” 列入七情之中。何為?道教六欲有兩種:與中醫(yī)同——風(fēng)寒暑濕燥火;道教義樞中的六欲——眼耳鼻舌身心。意味著“欲”隱藏在體內(nèi)而外觀在另一種渠道。如同《呂氏春秋》東漢哲人高誘注釋:“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你看,佛教“六欲”是由佛學(xué)經(jīng)典《摩訶般若波羅蜜經(jīng)釋論》提出:①色欲,②形貌欲,③威儀姿態(tài)欲,④語言音聲欲,⑤細(xì)滑欲,⑥人相欲。其魚我所欲,就是外露的狀態(tài)。所謂的金枝欲孽,人因?yàn)橛杏K成萬物主宰,由此葬送了自身。故而,佛教要求信徒不要有“七情”,即喜、怒、哀、樂、懼、愛、憎。乃是非之主,利害之根,影響禪定,使人無法修成正覺。佛教要求信徒禁止“六欲”,威脅佛性而難以修得真果,乃是一種潛意識(shí)吸收、遷移和逆向思維,從意識(shí)(左腦)返回潛意識(shí)(右腦),即為亞里士多德的反邏輯思維。相反,邏輯思維是認(rèn)識(shí)結(jié)構(gòu)過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能動(dòng)地反映客觀現(xiàn)實(shí)的理性作用的規(guī)律,又稱理論思維。如“厄洛斯”是參與世界創(chuàng)造的一位原始神,世界之初創(chuàng)造萬物的基本動(dòng)力,愛欲和情欲的象征,一切神靈情愛的的化身;但在柏拉圖之后,他被認(rèn)為是希臘愛與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羅馬名字叫維納斯,為九大行星中的金星)的兒子,一個(gè)手持弓箭的美少年。那么,一反一正,一動(dòng)一靜的陰陽變化,就是左右腦的互動(dòng),構(gòu)成了詩人難度創(chuàng)作,先從左腦(自我)中身邊的人和事取材、帥選和綜合,構(gòu)思右腦(本我)中的意象,在小腦(超我)的道德平衡中,形成詩歌的正向思維,如明喻中的文字表述,或局部的語言象征;反之,則是整體的主題象征,或意象派思維。所以, 不忘初心,才會(huì)堅(jiān)定追求,找對(duì)人生的方向,抵達(dá)自己的初衷。創(chuàng)造的秘密就在于初學(xué)者的心態(tài),時(shí)刻在新兵營(yíng)訓(xùn)練一樣,保持一種探索的精神;從前所有的甜蜜與哀愁、勇敢與脆弱、跋涉與歇息,原來都是在為了向著初來的自己進(jìn)發(fā)。

儒道美學(xué)上, 自我,本是一個(gè)小太極的最美畫像,但必然要將超我克己復(fù)禮,才能將七情六欲的四象,浮現(xiàn)出在造詣別人的時(shí)辰,也就同時(shí)造詣了本身,視為自救;從而恢復(fù)到原始本質(zhì)狀態(tài)的太極,本我也。如:日干占太極的人,為性為情,其天然的德行往往可以自貴,而闡揚(yáng)自我的功用,為功成名就,德行完滿之象,本我顯象也。這種本身就是本身的貴人,由于聰明并且堅(jiān)持,人生即使遭遇什么堅(jiān)苦和險(xiǎn)阻,往往也能自救。所謂的人人有太極。太極,便是一個(gè)靠近天人合一的大道。事實(shí)上,先天的清凈的“元神”,稱為性、命、真心,,后天的“識(shí)神”稱七情六欲,來自于人心的欲神(參),過度者,無法顯現(xiàn)元神(商),參商二星越走越遠(yuǎn),詩人的創(chuàng)作周期得到生理電路的阻礙,則會(huì)導(dǎo)致疾病發(fā)生。中醫(yī)上, ”神” 則是決定的強(qiáng)弱正氣為本的發(fā)病觀、治療觀,的主導(dǎo)。如脾藏意——存神,亦名思神、存思、存想,冥想等等,意謂存思人體之中、天地之間各種神靈。像“神失守位”是神受擾動(dòng)的發(fā)病重因,,影響氣和精,好比詩人的內(nèi)力是一種“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狀態(tài),直接損害人體。五行上:怒則氣上為肝木,喜則氣緩為心火,憂則氣聚、或悲則氣消為肺金,恐則氣下、或驚則氣亂為腎水,思則氣結(jié)為脾土;從而使臟腑氣機(jī)升降失常,氣血運(yùn)行紊亂,糟蹋精氣神的走向。反之,喜怒有常,不妄勞作,就能心安神定,需要通過心神-五臟神-身神”的合理調(diào)節(jié)。心神為神,生命之威儀,是統(tǒng)領(lǐng)五臟之神的最大神。其次,肝神為魂,本能也。肺神為魄,理性也。脾神為意,可控的思辨意識(shí)。腎神為志,不可控的潛意識(shí)(先天元神),天賦也,也就是詩人先天才氣的大小。 佛心上,出世而觀慧照了,入世才有能量的感應(yīng),自然也要修六妙門:一數(shù) 、二隨 、三止、 四觀、 五還、 六凈。大隱隱于朝,讓覺知在心靈細(xì)膩覺受境界中的復(fù)蘇——四空定(四禪八定)而辨六妙門。那心靈的感知而頓生空境,若是,感知凝固即時(shí)空為劫濁,則獨(dú)木難支而江郎才盡;反之,感知融解于心,則空境無可得,白光觀想,不為空境所束縛,宇宙我體,眾生我心,抵達(dá)五方佛國(guó)。如:金翅擘海,金翅:佛經(jīng)中所說鳥名;擘:用手把東西分開或折斷,如金藏云——金色的云氣裊裊生象而空無邊處,比喻文辭筆力雄壯。所以,在逆向潛意識(shí)的思維中,身體放松而自性壇城,淡然情懷就能漸次化空。如四喜四空:我執(zhí)、法執(zhí)、所知障就可能被破除,然后,賢圣層次而融入虛空。如:時(shí)光荏薦之后,會(huì)經(jīng)常聽到人們的仟悔:假如當(dāng)初我不隨意放棄,要是我愿意刻苦,要是我有恒心和毅力,一定不會(huì)是眼前的樣子,就是覺悟之后的逆向思維。如《二刻拍案驚奇》卷一:“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馱將來,也只是靠這幾個(gè)字,致得三教流傳,同于三光。”翰林學(xué)士蘇東坡奉命招待。自認(rèn)為是副絕對(duì)的遼使者出一聯(lián):"三光日月星",聯(lián)語中的數(shù)量"三"字,下聯(lián)就不應(yīng)重復(fù)。那么,無論你用哪個(gè)數(shù)目來對(duì),下面跟著的字?jǐn)?shù),不是多于三,就是少于三。蘇東坡對(duì)出的下聯(lián):"四詩風(fēng)雅頌。"妙在"四詩"只有"風(fēng)、雅、頌"三個(gè)名稱。原來《詩經(jīng)》中"雅"可分為"大雅"和"小雅"。 蘇東坡還補(bǔ)上三聯(lián):一陣風(fēng)雷雨、兩朝兄弟邦、四德元亨利。其中,《周易》'乾'卦里的四德應(yīng)該是'元、亨、利、貞';"最后一字是先皇圣諱,宋仁宗名叫趙禎,禎、貞同音,屬于"圣諱",故刪去一"貞",亦成妙對(duì)。妙,是后天知識(shí)的意象之度,善于嫁接,讓事物所達(dá)到圓融的境界,叫后得智。微,是先天能量的意境之玄,了悟天地的往來,但深?yuàn)W不容易理解奧秘,叫先得智。玄度,乃.佛法的玄妙的法理。詩歌的法理就是微妙之度,以靜制動(dòng),盈盈著圓覺思維之大哉。

心之凈土,詩之性情,如《觀無量壽經(jīng)》:“當(dāng)坐道場(chǎng),生諸佛家。"道場(chǎng)是詩的意境,佛家是詩人的心田。《朱子語類》卷七六:"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cái)啾娏骶洌ト搜哉Z亦然。"因此,什么樣的佛心就有什么的審美。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無法重來,記得初心。詩歌的脊梁是為民請(qǐng)命,經(jīng)常回頭望一下自己的來路,回憶當(dāng)初的起程; 經(jīng)常回到零起點(diǎn),將純凈的內(nèi)心,在審美的藝術(shù)旅程上,潛蓄而不著于外的德性,鑲嵌一雙澄澈的眼睛,那自然無為的德性,即為玄德,天德也。如小說家,散文家,詩人謝婉瑩,冰壑玉壺,人節(jié)操高尚而品性高潔,銅壺滴漏喻明月,其純潔明凈之心表露于一片冰心在玉壺,筆名:冰心,也就是太上老君的道德之初。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德不配位的人性,如同飛灰湮滅,雖然驚不起半點(diǎn)歷史漣漪,但誠(chéng)實(shí)守信的美德,翻動(dòng)的記憶,或許更為真實(shí)的性情而哭泣初心,正如一個(gè)新生兒面對(duì)這個(gè)世界一樣,永遠(yuǎn)充滿好奇、求知欲和贊嘆,是詩性成長(zhǎng)的內(nèi)在力量,給了詩情一種積極進(jìn)取的狀態(tài):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行,如同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使命,就是為中國(guó)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fù)興。 儒學(xué)上,詩歌是通過語言的感染力,從自我放大到大我的情調(diào)。如《孟子》所曰:“天下之本在國(guó),國(guó)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向度上,亞圣把倫理和政治緊密結(jié)合起來,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為仁政學(xué)說。如“親親”、“長(zhǎng)長(zhǎng)”的原則運(yùn)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jí)矛盾;維度上,強(qiáng)調(diào)道德修養(yǎng)是搞好政治的根本。如《禮記·大學(xué)》:“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guó);欲治其國(guó)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修齊治平”應(yīng)是“國(guó)人情懷”的語近指遠(yuǎn),從而讓孟郊的《游子吟》孝心,順著自然之氣而和諧天下。 就詩歌而言,思想的向度是個(gè)人潛意識(shí)的德行,藝術(shù)的難度是正反思維的對(duì)話。你看,那些來自書房的詩看上去老練成熟,好比中國(guó)新詩百年的詩歌教育來寫詩,那成千上萬同質(zhì)化嚴(yán)重的詩歌,卻少了鮮活的生活氣息和心靈沖動(dòng);宛如一潭死水的夢(mèng)想,還想侵占兩岸青山;讀不出詩人情懷、情趣、情感和深度的思考,那固定思維所囚禁的受累和審美的智知考驗(yàn),在綠水岸邊的巨石中,習(xí)慣思維的卵蟲依然孵成鯨群,跳出來大眾心理的怪圈。由此,詩歌同質(zhì)化的語境,沒有集腋成裘,道法自然,何來反向思維的仙情回報(bào)。 殊不知,詩有著高密度的飽和感,蘊(yùn)藏著地域、行業(yè)和生態(tài)里的精神浮想。倘若能從民間故事里的正向思維,更多的驚異化出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元素的逆向思維,即為潛意識(shí)的象外之象。那么,詩歌的神性,便會(huì)從精神的后花園的溪流上,就不用說,氣勢(shì),乃為來龍去脈而架橋設(shè)站了。維度上,吸引的泥土味和震撼草根性,在向度的宏觀視野里;風(fēng),以父為牛,就能扯倒任何一株古木的祖氣,人心浮躁也;雨,以我為馬,就能正覺任何一朵鮮花的靚麗,佛心沉靜也。詩,也就能通向小橋流水人家;伸展的才情衍射到扎實(shí)的生活根基,延續(xù)的纏聲,祈禱心田的稼禾生長(zhǎng),耙早稻田如同樂調(diào)中重疊的和聲,都將在鼓聲里“聽取蛙聲一片”;爾后,起承轉(zhuǎn)合,更替唐詩宋詞風(fēng)生死輪回。然而,回天無力的污染,用張愛玲小說中的一句話表述就是“我們都回不去了”。 也許春天激動(dòng)都成為一朵小花的生日,也許易逝的蝴蝶卻找不到莊周的影子,然而,詩歌的責(zé)任就是詩人的良知,雖然能說出笨拙的自由,卻驅(qū)趕不走一雙流淚的眼睛。那么,在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矛盾之中,讓消失的歲月一滴水也不剩,詩人依然舉起無形的旗幟。這,恰好是詩人寫作的難度,抵制現(xiàn)實(shí)的叛逆,在前意識(shí)(小腦)的超我中,回歸到理想的道性。無論是技巧上還是思維定勢(shì)上,都要了別正向思維的顯意識(shí)(左腦),反芻逆向思維的潛意識(shí)(右腦),如大乘一切諸佛瑜伽秘密金剛?cè)Φ馗窘?jīng)教以,清凈實(shí)相為宗,以真如法界為體。真理,是道家的虛無,為純碎的有,即為天上的實(shí)相;人間是假相,也為儒家的實(shí)象,佛教便曰: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但共同風(fēng)呼聲:人行善,按規(guī)矩辦事,無論是徜徉于自然美麗的風(fēng)景,還是埋頭于古老大陸璀璨的文化之中,把生命喂在詩里,在詩境中行走的過程,就能看見真正的自我,與中醫(yī)五臟之氣,借助后天的脾土之氣,像全真道的修金丹,回歸到太極嬰兒一樣,美學(xué)的人生將繪上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運(yùn)用在詩學(xué)里,北宋江西詩派的黃庭堅(jiān),提出的“點(diǎn)石成金”創(chuàng)作理論,,其要旨 在于強(qiáng)調(diào)詩人要在.學(xué)習(xí)古人詩文精華的基礎(chǔ)上,升華出新的詩歌意境,廣度有情;那么拙樸向后退的寫作,往小處寫初衷。看看題目就讓人會(huì)心自我,沾花一笑;視為器小易盈,器大易虧,致使在思維為陰的大海里;心同于虛空,虛室生白,惹去覺知有情人的頓悟,引領(lǐng)日出日落的靈波海面,在新時(shí)代的浪潮中,仿佛是靈性的文字,一行行,翻滾一波波的靈魂浪濤……

2019年10月3-4日吉林

作者簡(jiǎn)介:彭林家, 哲學(xué)家,畢業(yè)于東北師大中文系。中國(guó)散文詩作家協(xié)會(huì)副主席,中國(guó)散文詩作家聯(lián)盟評(píng)論委員會(huì)主任,中國(guó)詩歌在線吉林頻道詩評(píng)編審,國(guó)家一級(jí)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中國(guó)蕭軍研究會(huì)主辦的《當(dāng)代原創(chuàng)文學(xué)作品集錦》副主編,中國(guó)新詩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詩人, 2017年中國(guó)詩壇實(shí)力詩人。出版的著作有《裂開青云的紅冰》等,作品散見于《詩刊》《星星詩刊》《詞刊》《散文》《散文詩》《中華詩詞》《人民日?qǐng)?bào)》《中國(guó)詩詞年選》《中國(guó)詩歌年選》《中國(guó)百年新詩經(jīng)》《中國(guó)散文詩年選》《世界華文散文詩年選》《世界華文文學(xué)研究》《語言與文化研究》等100多種國(guó)內(nèi)外報(bào)刊,任多家媒體的顧問、主編和編委。曾獲全國(guó)散文詩征文及其他文體一二三等獎(jiǎng)。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duì)
反對(du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