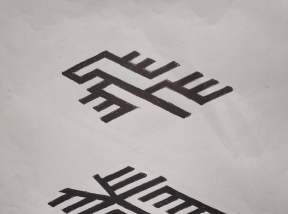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
在東汽將近四十年的生涯,本想在四川度過余生的我,轉(zhuǎn)眼也到了該隨風(fēng)而逝的年齡。如今,生活在幾千里路外的上海,回憶竟如此厚重,想“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恐怕也難。手機(jī)鈴聲一聲輕輕問候,心便頓時溫暖起來。在東汽企業(yè)文化的滔滔大河中,我很有幸成為其中的一朵浪花。漪漣雖小,但浪的歌喉始終是快樂的。即使是現(xiàn)在,我依舊能徜徉在夢想的路上,在大上海的詩歌之鄉(xiāng)—顧村,繼續(xù)從事著詩歌的創(chuàng)作,并擔(dān)任當(dāng)?shù)卦姼杩锏木庉嫞荒懿灰纤莸轿液汀妒锕狻肺膶W(xué)社和相應(yīng)刊物的夙緣。 我是從1979年開始寫詩的,比起70年代初就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東汽文壇許多老前輩來說,起步相對要晚,但離開東汽文壇的時間也晚得多,一直堅(jiān)守到退休之后兩年,其跨度將近四十載,自嘲自己已成為見證東汽文壇滄桑變化的“活化石”了。當(dāng)年的《曙光》刊物上曾發(fā)了我的第一首詩,題目是《時間篇》;還發(fā)了一篇散文,題目是《春天的歌》。初次投稿,便能一炮打響,心中頗有些自得,于是就勾起了我的創(chuàng)作**,一發(fā)而不可收拾了。那時的作品,從現(xiàn)在看來,無論是表現(xiàn)手法或是內(nèi)容的提煉,都是非常稚嫩和淺薄,但卻是許多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必經(jīng)之路。此后,我不僅寫過詩,還寫報(bào)告文學(xué)、散文詩、小說,甚至電視劇本,可以說患上了一種創(chuàng)作“饑餓癥”。我的大部分作品在《曙光》上發(fā)表了,例如小說《路》發(fā)表在1982年的《曙光》上,散文詩《在試驗(yàn)臺》發(fā)表在1982年2期的《曙光》上,散文《汽輪機(jī)回想》發(fā)表在1983年2期的《曙光》上等,其特點(diǎn)是均以工廠的生活為背景,對工廠的開拓和發(fā)展進(jìn)行贊美和謳歌。1982年3期的《劍南》(綿陽)上發(fā)表了我寫的詩《架線工》,這是我的第一篇外發(fā)作品。記得不久后,還專門和閆可亮去了一次綿陽,參加了劍南雜志社組織召開的小說創(chuàng)作會議呢。此后,就越寫越勤了,在省級刊物上發(fā)表作品的機(jī)會也多了起來。那些年,我寫的散文詩《海戀》發(fā)表在《星星詩刊》上,詩《天涯海角》發(fā)表在《青年作家》上,散文詩《拓路人》和《倒春寒》發(fā)在了《黃河詩報(bào)》上等,都應(yīng)該歸功于團(tuán)結(jié)在《曙光》文學(xué)社周圍文友間的良好學(xué)術(shù)氛圍。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