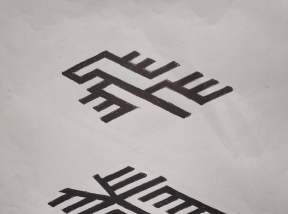中國(guó)是一個(gè)愛(ài)詩(shī)的國(guó)度,中國(guó)數(shù)千年的歷史,幾乎就是詩(shī)歌的歷史,每個(gè)時(shí)代,都留下了美妙的詩(shī)篇。歷代的漢詩(shī),以簡(jiǎn)潔形象的表達(dá),把自然的美景和人間的感情表現(xiàn)得豐富多彩,淋漓盡致,也把文明的進(jìn)展和歷史的屐痕鐫刻在音樂(lè)一般的文字中。這可以使中國(guó)人可以引為自豪,為我們的漢字,為我們的詩(shī)歌,也為中國(guó)人自由不羈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 上世紀(jì)初,中國(guó)的新一代文人發(fā)起文學(xué)革新,以白話取代古文,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風(fēng)起云涌,成為那個(gè)時(shí)代的新潮和時(shí)尚。中國(guó)新詩(shī),自上世紀(jì)初至今,已逾百年。一百年來(lái),中國(guó)新詩(shī)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了種種風(fēng)潮和跌宕,走出一條曲折而又獨(dú)特的道路。詩(shī)歌曾經(jīng)成為時(shí)代的先聲,喚醒沉睡的世人,也曾以異想天開(kāi)的意象,揭示人性的秘密。詩(shī)歌曾經(jīng)變成口號(hào)在人群中泛濫,也曾經(jīng)被人批判嘲笑,被很多人輕視忽略。然而漢詩(shī)美麗堅(jiān)韌而強(qiáng)大的靈魂,一直存活在新詩(shī)的潮流中。不管來(lái)路如何曲折跌宕,新詩(shī)一直在成長(zhǎng),在發(fā)展,在越來(lái)越多的人心中引起共鳴和回響,這種共鳴和回響,不僅是在中國(guó),也在向遼闊的世界輻射。新詩(shī)應(yīng)該有怎樣的面孔,應(yīng)該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發(fā)出怎樣的聲音?百人百調(diào),千人千腔,很難有一個(gè)權(quán)威的聲音統(tǒng)領(lǐng)詩(shī)壇。但是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現(xiàn)狀已經(jīng)證明,在我們這個(gè)有著悠久輝煌的詩(shī)歌傳統(tǒng)的國(guó)度,詩(shī)歌是不可能被消滅的。 上海是中國(guó)新詩(shī)發(fā)源和成長(zhǎng)的重要領(lǐng)地。一百多年來(lái),無(wú)數(shù)詩(shī)人在上海生活創(chuàng)作,每個(gè)時(shí)代都有重要的詩(shī)作在這里誕生。有人說(shuō),上海這樣的現(xiàn)代都市,不是產(chǎn)生詩(shī)歌的城市。我不能同意這樣的看法。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中的很多重要詩(shī)人,都在上海創(chuàng)作出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詩(shī)篇,譬如徐志摩、戴望舒、李金發(fā)、任鈞、辛笛、聞捷、蘆芒等。二十世紀(jì)上半葉,中國(guó)的很多詩(shī)歌流派曾在上海形成并繁衍,推動(dòng)了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的發(fā)展。上海一直是中國(guó)文學(xué)期刊的重鎮(zhèn),上個(gè)世紀(jì)上半葉,上海是中國(guó)新文學(xué)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重鎮(zhèn)和傳播中心,很多重要的詩(shī)人在上海生活寫(xiě)作,那時(shí)上海出現(xiàn)過(guò)各種形式的詩(shī)歌刊物,雖然發(fā)行量不大,但曾風(fēng)靡一時(shí),成為詩(shī)歌愛(ài)好者的家園。譬如徐志摩和邵洵美編輯的《詩(shī)刊》,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等人編輯的《現(xiàn)代詩(shī)風(fēng)》和《新詩(shī)》月刊,“九葉詩(shī)派”編輯的《詩(shī)創(chuàng)造》和《中國(guó)新詩(shī)》,這些詩(shī)刊,在不同的時(shí)期各領(lǐng)風(fēng)騷,展現(xiàn)了豐富多姿的詩(shī)歌流派。回顧那個(gè)時(shí)代上海詩(shī)壇的輝煌,至今仍讓人目眩。但是有一個(gè)現(xiàn)象,一直令人困惑,從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紀(jì)初,長(zhǎng)達(dá)半個(gè)世紀(jì)中,上海一直沒(méi)有一本正式的詩(shī)歌刊物。這曾經(jīng)使很多人感到困惑甚至沮喪。其實(shí),這五六十年中,上海一直是文學(xué)期刊的重鎮(zhèn),上海作家協(xié)會(huì)主辦的三家文學(xué)刊物《收獲》、《上海文學(xué)》和《萌芽》,都是國(guó)內(nèi)的一流文學(xué)刊物,歷來(lái)備受作家和文學(xué)愛(ài)好者的重視,國(guó)內(nèi)的很多重要作家從這些刊物起步被文壇注目。這些刊物,也發(fā)表詩(shī)歌,我至今仍記得少年時(shí)代在《收獲》上讀到聞捷的長(zhǎng)詩(shī)《復(fù)仇的火焰》時(shí)的激動(dòng)心情。《上海文學(xué)》和《萌芽》一直堅(jiān)持發(fā)表詩(shī)歌,建國(guó)以來(lái)數(shù)不清的詩(shī)人曾在這兩個(gè)刊物發(fā)表作品走上詩(shī)壇。但是,解放以來(lái)上海一直沒(méi)有一本公開(kāi)出版的專業(yè)詩(shī)歌刊物,這是一個(gè)事實(shí),也是一個(gè)遺憾。很多年來(lái),一直有人在提議呼吁,但很多年來(lái)沒(méi)有結(jié)果。上海難辦一家詩(shī)刊,大概是一直沒(méi)有好的機(jī)遇,也是很多人看輕詩(shī)歌的緣故。 在改革開(kāi)放的年代,《上海詩(shī)人》終于問(wèn)世,填補(bǔ)了一個(gè)缺憾和空白。《上海詩(shī)人》的前身,是一份詩(shī)人自辦的內(nèi)部發(fā)行的報(bào)紙,多年之后,經(jīng)過(guò)各方努力,成為正式出版的書(shū)刊,每二月出版一期,一年六期。我們希望把《上海詩(shī)人》辦成第一流的詩(shī)歌刊物,十多年來(lái)也一直在為此努力。創(chuàng)辦《上海詩(shī)人》的過(guò)程,是一個(gè)艱辛的過(guò)程,參與編輯的詩(shī)人,都是利用業(yè)余時(shí)間義務(wù)勞動(dòng)。不過(guò)這個(gè)艱辛的過(guò)程也是愉快的,因?yàn)橛辛诉@個(gè)平臺(tái),使上海和全國(guó)乃至世界的詩(shī)壇有了四通八達(dá)的接軌。十多年來(lái),《上海詩(shī)人》以自己別具一格的風(fēng)采逐漸被讀者熟悉喜歡,并得到越來(lái)越多的重視和來(lái)自各方面的支持。有人認(rèn)為,現(xiàn)在這樣的時(shí)代辦詩(shī)刊,是腦子出毛病,既無(wú)名,也無(wú)利,幾個(gè)寫(xiě)詩(shī)愛(ài)詩(shī)的人在那里辛苦蹦跶,就像和風(fēng)車開(kāi)戰(zhàn)的唐·吉訶德。這樣的看法,當(dāng)然可以付之一笑。在惟利是圖、唯錢(qián)為大的風(fēng)氣盛行時(shí),我們能辦一個(gè)和賺錢(qián)毫無(wú)關(guān)系的詩(shī)刊,這恰恰是文學(xué)事業(yè)有希望的表現(xiàn)。《上海詩(shī)人》的辦刊方針,是堅(jiān)持海納百川的品格,既扶植上海詩(shī)人,也面向全國(guó),乃至全球的華語(yǔ)詩(shī)人,在風(fēng)格上力求豐富多樣,不以編者個(gè)人好惡取舍,只要作品是詩(shī)人真情的抒發(fā),只要在藝術(shù)上有創(chuàng)新精神,就能在這里獲得一席之地。我們不可能讓所有人都來(lái)讀詩(shī),但我們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影響,辦好《上海詩(shī)人》,吸引盡可能多的讀者,并以此營(yíng)造高雅文學(xué)的氛圍,推動(dòng)中國(guó)的新詩(shī)創(chuàng)作。只要有詩(shī)人在歌唱,有人在讀詩(shī)誦詩(shī),只要詩(shī)歌還能引起人們的共鳴,能撥動(dòng)讀者的心弦,詩(shī)歌就不至于被邊緣化。千百年來(lái),詩(shī)歌從來(lái)沒(méi)有離開(kāi)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時(shí)代,依然需要詩(shī)。上海出現(xiàn)一家詩(shī)刊,并且擁有讀者和知音,這也可以看作是上海這座城市的詩(shī)意象征吧。 這本詩(shī)選,薈集了《上海詩(shī)人》自2007年至2017年的部分作品。十年時(shí)間,《上海詩(shī)人》先后出版了60期,發(fā)表各類詩(shī)歌逾萬(wàn)首,從中選出這樣一本詩(shī)選,是一次沙里淘金的精華之選。這雖然只是一本詩(shī)刊的選本,但也可以對(duì)中國(guó)新詩(shī)在這十年中的進(jìn)展和成就,做一次耀眼的呈現(xiàn)。 謹(jǐn)以這本詩(shī)選,回顧《上海詩(shī)人》的十年旅程,也以此紀(jì)念中國(guó)新詩(shī)的百年華誕。 (上海作家)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zhuǎn)播
轉(zhuǎn)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duì)
反對(du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