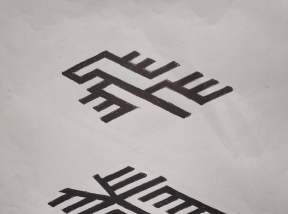C50D79D8-CB5C-4603-A6D0-D3A4A5F5D1DF.jpeg (0 Bytes, 下載次數: 5)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19-11-1 14:01 上傳
胡馬,本名胡君,男,漢族,四川廣元人。生于1970年。現居成都。供職于報社。曾參與《終點》《人行道》和《存在》等民刊。有詩歌、隨筆、小說見于《星星》《詩林》《詩歌報月刊》《四川文學》《青年作家》《草堂》《詩刊》《山西文學》等,作品入選多種選本。
胡馬隨筆:亡這首同題詩
0 九月到了,這收割季節,時間布置下來的作業,我必須得完成。 正如維特根斯坦對我們的告誡:“對于不可言說之物,必須保持沉默。” 但這道屬于我的難題,我必須解答。 我可以回避別人,但我總不能回避自己。 盡管,我一直在回避。 將這些流水賬付諸文字時,我思緒萬端。糾結,掙扎,不知該如何取舍。 有些人,要不要提?有些事,要不要回避? 尤其是我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巨細靡遺地剖析。 “未知生,焉知死?”圣哲拒絕給予答案,但他已經表明了態度。 在九月,一份關于秋天的自我診斷,我必須要硬著頭皮完成。 生活早已為我們揭示了存在的殘酷實質,只是我們一直不愿面對真相罷了。 我們用語言編織起保護膜,像鯰魚在周身涂抹的粘液,在這粘液的包裹下茍且偷安,仿佛暫時能應付外界的擠壓和逼迫,而一旦與現實正面遭遇,所有在內心構筑的幻境,立即碎成粉末。 我們既不能為了所謂的未來透支現在,也不能在對無力挽回的過去的懊悔中荒廢時日。 但是,舍此,我們又能怎么辦呢? 什么是蹉跎歲月? 現在,終于明白,我們生活中虛度的每一天,都是。
1 9月20日中午,陰轉晴,天很藍,晃得眼睛疼。 蜀地少有的好天氣。 前往府城大道的途中,在疾馳的出租車上,我和廣外的何光順教授一路交談。 當我偶然說起一位詩友死了時,忍不住潸然淚下。 我趕忙把臉轉向一側。 我說的,是吳建軍,一位畫家,兼詩人。 短時間的沉默后,關于南方詩群和珠江詩派的話題,在短暫中斷后,很快重新恢復。 何光順說到廣東詩人溫遠輝,對他編選《南方詩選》給予很多支持,其時正在ICU病房搶救。(就在我正在鍵盤上敲這些文字時,從廣東詩友的朋友圈傳來了溫遠輝去世的消息。) 話題切換到我們一直交流的寫作方面。 到達目的地后,我們坐在有落地窗的房間里,邊喝茶邊聊。 陽光照徹。死亡這個沉重的主題,再未提起。 嗯,死亡這首同題詩,我真的沒有準備好。 如何起筆,如何破題,如何完成,這個大課題,需要我耗費一生的時間去思考,去面對。
2 一個月前,8月20日,馬永波由渝抵蓉,我利用中午時間跟他匆匆一晤。 我跟他微信加好友后,交往幾年了,這是第一次相見。 聊起江南人事,我提起幾年前孟原讀到江南梅的一首詩時,大為推崇,還當場推薦給我。 他眼睛一亮,有些意外,說沒想到孟原會關注到江南梅。 神色繼而暗淡,說,她已經死了。 我一時不知道如何接他的話。 頭天晚上10點,他在寬窄巷子喝茶,約我相見我正在上夜班,走不了。等我下夜班,差不多已快凌晨1點,問他,他說不敢熬夜,已經回酒店。 回家后,再一次通宵失眠,直到天亮才睡了一陣。 我每天的時間,被各種臨時或固定的鬧鐘分割成零碎的片斷。 沒想到,那天連提前設的鬧鐘都沒聽到。 當我滿臉倦容衣著邋遢趕到他下榻的酒店時,已經到了午飯時間。 我們就在街邊一處小館子很簡單地吃了一頓飯,太過失禮。 當時反應遲鈍,頭昏昏沉沉的,對這生死之間的遽然轉變,有些不知所措。 因詩之緣,有幸聽聞一位陌生詩人的名字。源自歷史、地理和文學的江南,一下子變得親切、具體和真實可感。雖在三千里外,心中到底多了一絲光亮。期盼因緣際會,未來哪一天,說不定可以相見。 誰知歲月倏忽,再聽到這個名字,竟成永絕。 未來?對有些人來說,再也沒有了。
3 吳建軍的噩耗,是詩人張衛東告訴我的。 那天是9月9日,星期一,一個成都特有的陰天。 陪女兒在培訓中心上舞蹈課時,正在閉目養神,張衛東打來電話,說:吳建軍死了!…… 我愕然。 一旁,另幾位陪孩子跳舞的老人們正在低聲交談。我趕忙從大廳躲到外面的電梯間。 無法強作鎮定,我盡量一字一句地,以非常笨拙、非常遲鈍的語氣,對張衛東說:我們,無論遇到多么大的挫折,都應該努力尋找溫暖和光明,實在支撐不住,該向朋友開口求助就開口……說著說著,不禁語塞,淚下。 其實,我這是在說給自己聽。 幸好那個時間段,電梯附近沒有旁人上上下下。 不等7點30分舞蹈課結束,下起了大雨。妻子開車來接我們回家。 匆匆吃完晚飯,雨停了,急忙趕到舞蹈培訓中心,騎上先前留在這里的自行車,到報社上夜班。 被生活奴役,腳步即使生銹了,也不能按下暫停鍵,只有死亡才能下達停止前進的命令。 又是一個無眠之夜。 輾轉反側中,希望第二天起來,會有人告訴我:關于吳建軍的死訊,不是真的。
4 如果當初海子居住和生活在成都,他大概不會選擇臥軌吧! 這個跡近狂悖的觀點,是我一度在內心堅持的。這執念,源于我對成都的信任和偏愛。 成都被詩歌江湖稱頌為“詩歌首都”。 我一直不以為然,一來詩歌不需要所謂首都,二來成都的現狀,實在當不起這樣的名頭。不過是有意無意地配合了成都的城市營銷罷了。 其實,我更欣賞的是它的另一個名號:詩歌的最低處。 松馳,自然,平和,親切,包容,無為而無不為。 詩人多,詩會多,尤其每一次有外地詩人到訪,都成就了詩友們飲茶喝酒吃肉的聚會。 身在成都,還是難免為它護短:詩人之間的情誼,總還是溫暖的。 何況,成都酒濃,茶香,人親切。市井生活的煙火氣,多少總能消解一些象牙塔的高冷和金字塔的壓抑。 作為一個辦公室囚徒,在壓抑沉悶的籠中待久了,即使參加最輕量級的詩會,也相當于一次放風。雖然這放風并不徹底。 在成都,這種放風的時候,很多。 但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多么盲目、幼稚和可笑。 正是在到四川尋求溫暖和慰藉時,海子遭受了最后一記重創。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早已成為房地產廣告金句,“目擊眾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也因民謠歌手的傳唱而風行一時,但在這兩種相互對立的精神景觀之間,誰能聽到他作為一個詩人的絕望、徘徊和掙扎?
5 吳建軍比我小幾歲,寫詩時用的筆名是“地主”。 那時,人行道詩群的兄弟,隔那么一段時間,就要相約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地點或者是川大工會,或者是寬窄巷子,或者是后子門附近的白果園,或者人民公園鶴軒茶社,或者琴臺路附近的散花樓和臥梅軒,或者獅子山上的槐樹林。 吳建軍眼神清澈,面容沉靜。一起喝茶時,話不多,神態安穩。不時跟兄弟們回應一下,說起話來語調平緩,帶著不太明顯的樂山口音。 他的詩寫得很好,語言干凈漂亮。我至今記得,在我輪值編《人行道》時,編發過他的一組詩,題目是《上海,上海》。 聽說他在2008年以前,賣畫掙了錢。后來他搬到藍頂,修了一幢屬于自己的畫室。 成為簽約畫家之后,因為投入創作的原因,他跟寫詩的朋友們不再怎么見面,但大家都為他成功簽約而高興。 但2008年后,隨著經濟急轉直下,國外藝術市場萎縮,很多中國畫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除了外部因素的逼迫,他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創作路線,對身心構成反噬,或許也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吧。 死亡隨時在拋灑誘餌,我們這些在生活中銜枚疾行的人,吞鉤只是早或遲而已。
6 中秋前夕,一個悶熱的下午,參加完《草堂》詩刊組織的中秋詩會后,我與詩人凸凹、呂歷、李龍炳、山鴻和桑眉等步行至新華公園喝茶。 大家好久不見,樹蔭下,茶香里,談興頗濃。話題切換中,呂歷向我們科譜起了抑郁癥,關于失眠,關于不合群,關于厭食,關于情緒失控,關于肢體行為變化,關于自責與自罪。 每一樣癥候,都那么嚴重地符合我。 曾經,休息日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陷入木僵狀態。房東老太太勸我說,你去約你的朋友們喝茶吧!我當時還奇怪她多管閑事。現在想來,大概她看出我狀態堪憂吧。 曾經,坐在出租車副駕上,司機緊張地對我說,兄弟,我咋覺得你很焦慮呢?我不信。他調整后視鏡讓我看。我不記得,自己在后視鏡是怎樣一副形象,但司機當時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曾經,下夜班時,正好遇到剛剛一起編版子的值班領導開車經過,他停下車,望著我,我望著他,僵持十幾秒鐘,我大腦一片空白。哪怕出于禮貌打聲招呼,也能化解當時的尷尬。 曾經,妻子到單位來跟我一起去外面吃晚飯。長期上夜班,我們好長時間都沒面對面地說過話。就在她一邊很興奮地說著話,一邊挽著我的手臂往街上走時,她突然停下來,望著我的臉,說這么久不見,你擺臉色給誰看,“哇”一聲哭著跑遠了。剩下我站在報社院子里如墜五里霧中。 就是這樣,我長期處于危險之中而不自知。 長期夜班導致的慢性疲勞,讓我反應遲鈍,暴躁,易怒,并伴有嚴重的拖延癥。
7 我去過吳建軍的工作室,跟李兵一起。 2006年到2007年,我先后在成都晚報和一家汽車雜志上班,那時我住在肖家河。 吳建軍的工作室與我的住處相隔有一段距離,但并不遠。李兵任教的西南民大也在這一片。 印象中,好像是連綿陰雨后的一個下午,院內陰冷、潮濕,有一株長得很好的芭蕉,跟我租住的院子相似。 我們在院子里喝茶,聊天。然后到他的既是工作室也是家的出租房里,欣賞他的作品。房間里,光線很暗,那些掛在墻上的油畫,色調尤其顯得晦暗、壓抑,仿佛一個個夢魘。我記得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男人,卻長著一雙鳥腳。 我感覺,那些作品是畫的我自己。 不得不說,他的繪畫作品畫出了我內心深處的絕望和焦慮,而這,一直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 當時,我內心極其不安,不得不跟吳建軍和李兵提前告辭。 在平靜外表下,他一定是跟我一樣有著同樣不安的內心世界吧。 吳建軍的畫帶給我的審美體驗,像極了杜力帶影碟《索多瑪的72小時》來我那里觀看時的感受。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女朋友何雋。 那時,2001年到2003年,我在成都日報上夜班。我租住在落虹橋一處老院子里,直到2006年。 那是我看過的最讓我接受不了的電影。 也許,我脆弱的審美觀,還沒有準備好面對一部真正的藝術電影吧。 杜力還帶過別的一些電影來,其中有一部《石榴的顏色》,我非常喜歡。薩雅諾瓦,愛和死亡,在平靜的敘事中令人迷醉。 后來,我還租了塔可夫斯基的《鄉愁》,反復欣賞。 死亡在放長線,而我們,誰是它要釣的那條魚?
8 況璃去世了! 昨天,9月27日下午。當從朋友圈看到這不幸的消息時,我正在地鐵上。 8月份我還去他辦公室跟他聊天呢。當時,他正在為自己負責的《文旅》雜志物色主編。我幫他推薦了兩個人選,但并未談妥。此前,詩人席永君在他那里任執行主編。 平時跟況璃交往并不多,前些年在一些詩友參加的文藝活動中,我們不時會見面。他給我的印象是,說話聲音洪亮,熱情洋溢,充滿干勁。 聽說他從體制內出來后,曾去云南經營橡膠種植。 2014年,他在孵化園運作一個文化傳媒公司,2015年,他在成都高新區運作一個跟詩歌有關的新媒體平臺,先后曾邀我去觀摩交流。 一位了解內情的媒體兄弟說,況璃是詩人性情,但雜志投資人是商業頭腦。不能喝酒的況璃,**著在酒桌上喝了不少酒。 正當盛年的況璃,離開得太突然了。 “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大詩人博爾赫斯說。死亡于他而言,視若等閑。 “秋天啊,秋天取走燃燒的人”。李海洲在《秋天傳》中如是感嘆。 我們都在燃燒,只是這燃燒的火焰我們看不見,在我們的骨骸和血液深處,它消耗著我們的生機與活力。 難道,我們要活得像博爾赫斯那么老,才能將生死置之度外?
9 2003年3月,杜力和何雋去了北京。當年稍后,趙嵐去了上海,先后在東方早報、第一財經日報等媒體做記者。8月份,高嶺去了北京。2003年是一個離別的年份,一度,我也想離開。 我2004年采訪北京國際車展時,在高嶺位于南五環郁花園的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去看了杜力和何雋。他們與人合租在花家地一個筒子樓。杜力給我煮了好大一碗白菜面條。吃完飯,他騎著自行車馱著我穿街過巷去看何雋。那時何雋在萬夏的文化公司上班。在公司附近的花壇邊,我們三個人,坐著,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太陽把火炬樹的影子投到我們腳下,很好看。 杜力后來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當編輯,直到前年,為了孩子,重新回到成都。此前,他和何雋離婚了。 那次在杜力家吃飯時,他把馬雁在北大讀書期間的油印詩集裝進我的背包里,讓我帶回成都。 馬雁在北大上學時,詩就已經寫得很好,冷靜、干凈,自成一格。 我跟馬雁算不上朋友,但我們有幾個共同的詩歌朋友。雖然同在成都,但見面總共只有三次。一次是幸福劇團的兄弟們在培根路附近喝酒,人很多,有冉徽川、程烈、韋源、李兵、杜力、蕭瞳等,我記得馬雁也在,那時她還沒去北大。我對酒只是淺嘗輒止,再加上第二天還得采訪,提前離開了。第二次是在寬巷子喝茶,在座有李兵,還有別的幾位兄弟。那時寬窄巷子還未打造,沒有成為網紅打卡地,保留著真實、樸素的市井面貌。馬雁很安靜,話不多,跟她在網絡論壇上言辭犀利觀點激烈感覺不同。第三次,是在成都傳媒集團行政辦公樓走廊上遇到她。我去辦有關社保的手續,她那時在成都傳媒集團行政部門上班。 直到2012年冬天,突然聽到她的噩耗。 那是一個工作日的午后,天很冷。朱曉劍突然打來電話:馬雁你認識嗎?我說認識啊,剛剛還跟他在報社后面一起吃飯。我說的是馬彥,也叫馬明明。甘肅80后詩人,剛從西藏到成都找工作。我想把他推薦給我當時就職的華西都市報,但最終沒有落實。 朱曉劍一時語塞,半天才說:馬雁死了,在上海…… 我站在街邊久久回不過神來。 馬雁的死,讓我一直對她的朋友們耿耿于懷。在她真正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都在做什么? 或許是我過于苛責了。 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這是宿命,誰也改變不了。 前不久,跟趙嵐聊起馬雁,他說當年馬雁的父親到上海料理后事,他陪老人家住在酒店,一夜未眠。 離開成都去上海后,趙嵐在媒體發展得很好。2008年汶川地震后,趙嵐回四川采訪,我陪他一起去三星堆博物館和綿陽九洲體育館采訪,當時是鐘鳴開的車,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回成都后,我還陪趙嵐去省民族宗教研究所采訪民族學家李紹明先生,采訪的主題是羌族的歷史和發展現狀以及未來。 期間,我和他得空就在天涯石北街喝茶閑聊。 2014年我去上海時,在趙嵐的家里住了一夜。
10 其實,死亡并不是突然來到的。 “生活就是一種緩慢的死亡。”拉金直指我們平庸生活的真面目,可謂一針見血。 死亡,因為來得緩慢,令我們缺乏足夠的警惕和洞察。 正如聶魯達所描述的那樣:每個人面臨的不是一次死亡而是許多次死亡:/每天一次小小的死亡…… 只不過,當這些“小小的死亡”走近我們時,我們或許并沒有意識到,或者不屑一顧。 但是,一旦當它開始加速,我們就會猝不及防。 獅子山上那些槐花,每年春末夏初,它們開花,它們凋謝,盛開和消融,都像一場雪,成為記憶中的風景。 但我們不覺得這盛開會被錯過,不覺得這凋謝會成為永別。仿佛時間是取之不盡的,今年錯過了,反正明年還有春天。 直到有一天,它們被房地產業連根拔起,甚至連那片丘陵也消失了,再也不會出現。 地震后的某個周末,那片曾經槐花如雪的地方,我和干海兵站在那里,憑吊我們再也回不去的往昔。 按弗洛伊德的理論,每個人身上都存在著死亡本能和生本能,這是與生俱來的。死亡本能就是要摧毀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態的沖動。 如果把一個人比喻成一棵樹,一棵獅子山上的槐樹,那么,到了秋天,我們是否也需要用生本能抑制住生命中的死亡本能,像樹一樣抖落一身枯葉,為來年的生機儲蓄生機和力量呢? 而今識盡愁滋味,卻道天涼好個秋! 人到中年,夫復何求。 也許某天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身處另一個世界了。 但,在還未到大限將至的時間里,我們身心的積垢,必須被肅清,好輕裝上路,迎接更嚴酷的寒冬。
《致無名雕塑》
他渴慕陰影甚于記憶,但大海 卻潛入街道下面不肯現身。 被褫奪的呼吸,需要一雙翅膀 才能廓開城邦面孔上的夜色和銅汁。 “伊卡洛斯,伊卡洛斯 你怎么在飛翔中遺忘了 后天習得的僭越天空的禁忌?” 他下垂的肢體向島嶼折射著哀鳴: 父親,請徹底放棄我吧! 太累了,而歸途太過遙遠。 想到您的告誡,但一切己來不及 鐘聲回蕩時故鄉就被收回! 我只能以海水為塵土,雖然 那些海水沒有您調制的蠟溫暖 ……現實和他的**之間,只有光 在雕琢昨日的鏡面:此時 誰仰望星空,誰就是悲劇的制造者。
《瓷語》
“難道是一場薄雪埋葬了呼吸?” “其實,那是天堂和我們之間的距離。” 如光沉入水面,當我負重潛入 向著天空上升的遂寧,內心的折射 召喚我從霧霾中驚醒。而你還在 時間的天青色封釉里俯身勞作。 耕織的游戲,是謊言說出的真理: 蓮瓣,梅,菊,忍冬和牡丹…… 你種植的草木,在爐火中怒放 你養的鳥獸蟲魚,在倒影里奔跑。 從卷草到纏枝,天空的顏色 是通向神明的唯一過渡。推開 辛亥年的窗戶,我看見春風浩蕩 若耶溪在你身上行使一場大雪: 在陶輪、風波亭和崖山海邊 在樓船、武信城和撒馬爾罕的曠野 在生之獨酌與死亡對飲轉換的間奏 ……狂舞如屠城的戰旗。 而博物館的冷光燈,將一個王朝 輕輕推至歷史最易擱淺的險灘。 北風越過等高線,當蒙古鐵騎 自地底涌出,將鐵鉤銀劃踏碎 多少美淪為灰燼的囚徒。只有你 將不可觸摸的根須,沉入苦難之雪 在不被命運捫及的暗處,沉睡如挽歌。
《梯子上的荷馬》
一切都在想像中完成:他 把天堂布置成一座有旋轉樓梯 的圖書館。紙、灰塵和印章 掩蓋不了他身上的烏托邦氣息。 在書架間潛行,以平靜的鰓 過濾庸常時日,他像海馬 忘記了海上風暴。當他坐在梯級上 一部無人借閱的編年史被攤開 充滿遠離時代的情節和敘事張力。 天使們上上下下,不在乎 是否打擾到這個正在休息的上帝。
到手的一切榮譽被他嚴辭拒絕。 幻想和記憶構建的迷宮,從反向 阻礙他回到現實,但他樂于 將自己囚禁,享受想像中的漫游。 作為**者的棋盤,亞美利加 你孕育的木材有神賜的花紋和香氣 適宜批量加工槍托,但唯有 這一支幸運,成為他手中的鉛筆。 在記下夢境、**和血腥的瞬間 父親借老虎的咆哮發出告誡: 快丟掉羅盤!怎么還在地獄徘徊?
通過失明無限接近真理,他成就了 自身的不完美:點亮天空并成為 其中最耀眼的星辰。對記憶 進行的歸納已很充分。 噢,請原諒無盡歲月的饋贈 它給予一切,又將其無情剝奪! 當渾身上下,只剩假牙是真實的 恍惚間,他聽見陰影中有人召喚: 荷馬,動身吧,時間到了! 他靜默成一尊胸像,未失明的 那只眼球,轉向人們遺忘了的東方。
《入夏》
他的夏天始于一場葬禮。 從祥和里去玉雙路,繞道天祥街 比從一環路過去要遠些。 不再寫信的年代,他懷揣 一枚牛皮紙信封出門去叩問夏天。 他不是去郵局,而是去 參加入夏以來的第一場葬禮。 是的,他的夏天始于這場葬禮。 邁著木偶的步伐踩過街面積水 每一步落下,水花濺起(他 陷入回憶:一塊用舊了的馬蹄鐵 在鐵匠的鐵砧上動情歌唱 失去的月牙在火星蕩漾中現身) 銀行門前,鎮墓獸蹲伏如火犬 辨認著飄過它眼前的每一幅面孔。 城市和天空的倒影碎了又迅即 恢復舊貌,在他不能轉身的年紀。 “像一滴淚水消失在雨中。”① 在奔行往返的傘群里,他 與類似的人就這樣被分割,包圍。 當然,還有更多的事不可言說 比如疲倦、麻痹和遲鈍 太陽穴的跳痛、灌鉛的關節 以及沉默和洞悉世事后的決絕。 他和他自己漸行漸遠,仿佛 垂釣者與白鷺之間彼此視若無物。 不能將更多消息裝進信封了 十年沒有收到過來信又怎樣? 遠行者上路,任何行李都多余。 況且,他并沒有什么事情 需要向死者帶去落花的口信。
注①電影《銀翼殺手》中的一句臺詞。
《在蝸牛農場過周末》
跨過鋸齒溪,在機耕道盡頭 蝸牛農場伸開了觸角,用池塘 和梯田迎接他們一家的到來。 “必須有露水和蟲鳴。”這是他 年初就許諾給女兒的周末禮物: 上帝給她的豹紋,烙在蝴蝶身上 她可以觀察,卻不可以玩火; 羊在低頭吃苜蓿,偶爾抬頭 揣摩他們眼中源自霧霾的妒意; 過了采摘期,她仍然闖入茶園 提著籃子,一心想當采茶工…… 但,這一切都只是插曲。 藍莓熟了,年輕情侶們發現 農耕生活可堪夸耀的浪漫主題。 日光賦予那些果實以藍色火焰, 植株的行間距容得下他的肺活量。 站在田壟上,他嘗了一枚 很淡,遠沒有超市賣的 那么甜美、可口,且顆粒飽滿 離成熟似乎還差最后幾天日照。 夜里,他夢見六百里外的老家 女兒牽著他在松針上散步像牽著 一位盲人在上帝睫毛上跳舞。 他們一邊攀登一邊向天空拋藍莓 那些黑色的貢果 曾在米倉山的越橘樹上燃燒。
《熱屋頂上的貓》
夏天謝幕時,屋頂向茶杯敞開 盆中的曼珠莎華夢見下一個花期, 雀鳥暫時放棄了樹冠上的旅程。 身為貓和薄荷的主人,他向天空 借來這片長滿蔬菜和瓜果的園圃。 隔著矮墻,他指著不遠處 動車輕輕滑過獅子山,把秋天 從綿陽運往三蘇祠。更遠處 一片積雨云悄悄收藏起龍泉山脈。 坐在瓜架下,他們談到邊疆政治 民族學和宗教史的鹽分。談到 工資的含金量和房價的火色,顯然 它們比理想具有更高的回跳硬度, 且始終充滿暴烈的閃電和火花。 兩個小女孩圍著他們玩輪滑 像兩句詩行在互相追逐,不時 撞到他們身上,讓暖瓶和話題 處于危險的境地。她換下的乳牙 成為樂譜上并非多余的休止符。 而她跌倒時撞裂的嘴唇已被縫合。 她熱愛的真理是帶格子的連衣裙, 而她熱愛的游戲是一個人跳房子。 貓趴在地上,用臉推著嬰兒車 向一株三角梅無限靠近。他暗想: 歷史的車輪能否用臉去推動。 他們是獅子,但己被生活馴服。 站在屋頂上,看這曾經的郊外 早己成為城市擴張后的繁華一角 卻看不到腳下被魚鱗般的高樓 牢牢釘住的獅子山。當黃昏逼近 他說歷史正處于青春期,隨時 有懷孕的可能。而他說詞語是迷宮 是他的父母之邦,即使永不能返回。
《彩虹和糖》
這無盡歲月中平凡的一日, 他和女兒沿堤壩騎了小半個弧形。 頂戴灰燼的蘆葦閃過,讓他想起 某位詩人已提前融入暮色。 熟識的鷸或灰鷺,像鄰居 豎起舊耳朵,出于社區禮儀 對他們的到來沒有做出任何反應。 “爸爸,我們的鈴鐺為啥不響?” 她的童車是啞巴,他的單車亦然 沉默是趨勢,她小小年紀不懂。 作為觀鳥者,他們錯過了 最好的季節:候鳥早己上路 像星辰消失于城市上空的霧霾。 “爸爸,我怎么從來沒見過彩虹? 你上夜班時都做成彩虹糖了嗎?” 他己很多年沒看到彩虹了。 急趨或靜立,都需要勇氣 狼蛛在他們身上筑巢,它的復眼 是否把他們當成廢墟中的風景? 哦,廢墟,他熱愛它的寓意 甚于廢墟本身:在東郊 工廠紛紛把煙囪伸向天空深處 將滿腔墨汁倒向云端。那些 倒插的吸管,曾經將彩虹和蔚藍 舔食一空。如今,它們 被魔術師用咒語搬到了遠郊, 但帽子上偶爾出現的晴朗 并沒有他們心中想像的那么遼闊。
《車過簡州》
過了簡陽,光的重量在消失 空氣傳播香甜的教義。 為避免心愛的餅干——那些 小魚或熊,那些平原上的圖騰 ——被他嚴厲禠奪,她 將它們掰成顆粒。即使是 河邊最年幼的鷸鳥,也可以吞下。 這些雪,這些**的碎片, 這些星星的余燼易于被時間收藏。 童年饑餓史在記憶閃回。當動車 滑入隧道的瞬間,仿佛永夜 提前降臨。哦,一轉身 就是一場分離而接下來 每一分每一秒又在與世界重逢…… 車窗外,燈光漸漸黯淡、熄滅 卻重新在她的瞳孔里閃爍。 突然有一種不舍,自荒涼軌道 向天空上升,生生撞響 冬天的胸腔。他暗自懊惱: 或許真的應該像他們一樣 在四十歲出頭就長出兩道壽眉, 在兀自年輕的眉弓上。 “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電掣風馳中,穿**的孟子 醬香型嗓音發出穿越合金的告誡。 但他想,雙雙放棄總是可以的吧!
長淮詩典新增名家點詩欄目
《名家點詩》可評一人多首,也可評多人各一首(3人為基數) 該欄目將結集出書,歡迎詩人、詩評家把好詩好評砸過來! 投稿郵箱:chsd998@126.com;330513284@qq.com 投稿須知:好詩/好評+簡介+照片
《長淮詩典》顧問
梁小斌、陳先發、余怒、李云、楊四平
主編 雪鷹
編委會成員(按姓氏排序)
阿翔、方文竹、宮白云、慧子、盧輝 林榮、劉斌、李不嫁、裴郁平、盛祥蘭 少爺、汪劍釗、向以鮮、雪克、雪鷹 西棣、育邦、楊啟運、張潔
編輯部主任 少爺

9F1DAA30-8EEA-4845-AAD0-F1B4BB3C974E.png (0 Bytes, 下載次數: 6)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19-11-1 14:01 上傳

A8C7D753-0552-4934-AC1B-616EA1D8CC8C.png (0 Bytes, 下載次數: 9)
下載附件
保存到相冊
2019-11-1 14:01 上傳
《長淮詩典》公眾號欄目簡介
一、名家點詩:著名詩人或評論家為著名詩人、實力詩人、新銳詩人點評詩歌三首以上,可多人點評一人,亦可一人點評多人。
二、實力詩人三人行:由編委會成員薦稿,每次三位實力詩人,每位詩人詩作5-10首。實力詩人亦可直接與編輯聯系。
三、專輯:已成風格的詩人詩歌5-15首,詩論或者他人評論若干,附照片、簡介一并發郵箱 chsd998@126.com;330513284@qq.com
四、詩群大展:以地域或詩歌社團、詩歌群落為單位,每期10-20人,每人3-5首詩作,帶個人簡介,以及200字左右的詩群簡介,說明詩群代表詩人、詩群流派風格、詩群刊物、創作成就等。作品資料發郵箱 chsd998@126.com;330513284@qq.com
五、投稿須知:同意本公眾號原創保護,特殊情況需事先聲明;Word文檔,小四號宋體,左對齊,標題加粗。
《長淮詩典》編委會 2019.5.29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詩歌出版中心(常年)征稿啟事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是國內文藝類圖書出版一流大社、名社。是一家具有廣泛文化影響力的文藝出版社,被譽為當代文學出版重鎮。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堅持原創、精品、格調與傳承的出版理念,“薈萃八方精英,力推百家佳作,重視文化內涵,追求高雅品位”。在長篇小說、大家散文、紀實文學、傳記、作家文集、名家詩歌、言情小說、學術精品等諸多領域具有專業優勢,逐漸形成文學、文化、教育三大核心板塊。近年來,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既具有社會效益,又具有經濟效益的優秀圖書,在國際國內各類評獎中榮獲一系列大獎。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詩歌出版中心,秉承品質與服務并舉,專業和情懷并重的理念,向您提供設計制作、出版印刷一條龍服務。歡迎有意出書的單位和個人(單書或叢書均可)聯系我們。我們將竭盡全力為您服務!
聯系電話
雪 鷹 18915871239 劉蘊慧 13913967609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詩歌出版中心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播
轉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