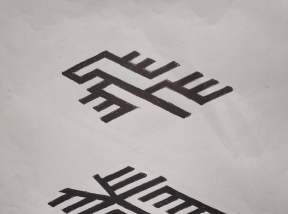|
嚴寒,男,早年游歷北方各省,做過礦工、鍋爐工、茶農、教師,現定居江南長江邊小城。詩文?見巜詩刊》、《詩江南》、巜揚子江詩刊》、《重慶文學》、巜西部》、《雨花》等各刊。
 嚴寒:六月之詩
竹笛
你用絲巾擦我的竹笛 冬夜的風又黑又硬 像那把砍竹子的刀
你傳來的音信是一壺燒酒,和 一片樹葉 你穿著一件霞光織就的衣袍 你低聲地抱怨: 我送你的竹笛 你從沒吹響過
釆野山楂的姐姐
下雨了,姐姐,雨像鑼鼓聲 從天空落下來 我們沿著山脊越走越遠 一大片野山楂點燃了一面山坡 下雨了,姐姐,云霧從谷底涌上來 云霧帶著苦艾的氣味,新灌漿的 麥子的氣味,從谷底涌上來
姐姐嚇哭了 一邊哭一邊抱著我說: 別怕別怕,有姐姐呢
那場雨沒有停過 不是我在回憶那場雨 是它在回憶我 在它濕淋淋的記憶里 有兩個在雨霧裹挾中 相擁哭泣的孩子
我帶走了那面 長滿野山楂的山坡 幾十年來我一直帶著 揮一揮它,野山楂就雨點般落下來 抹一抹它,云霧就從谷底涌上來
果馬河
如果我把這山谷譜成曲調 那果馬河是一段慢板 (六月除外,六月它會變得瘋狂) 把黑暗擋在眼睛之外 它就一個夢,一個狹長的 閃光的夢 (六月除外)
你還要忘記 山洪曾帶走嚴中翠,和 她兩個放學的孩子 忘記轟然倒塌的十隊橋
你要在一個有青草香味的夜晚 走過河灘,把繁星閃爍的天空 戴在頭上
雪落在果馬山谷
雪落在果馬山谷 用它的黑夜之手 撫摸我 也撫摸樹林,和山腰里 兩間廢棄的搖搖欲墜的老屋 天空的灰塵 掩埋了山谷
許多人走了 還有人正要離開 像這場被風驅趕的大雪
大王嶺已經看不見了,而大陰山 是一頭正在分娩的獸 痛苦地趴在 亂雪飛舞的夜空下
楓樹的果子
祖屋后面有一棵大楓樹 幾個人合抱的大楓樹 每年上面長滿刺猬一樣的果子 冬天樹葉落了 那些果子不肯落下 像樹枝吊著一只只小刺猬
一年春天刮了一夜大風 外婆說:快起來 去屋后撿楓樹果,回家當柴燒
大楓樹下落了一層黑色的果子 幾只小喜鵲,在地上撲騰 它們粉紅的肉翅上,只有幾根羽毛 還不能飛起來 昨夜的大風吹翻了它們的巢 它們一面撲騰翅膀 一面驚恐地大叫 聲音絕望嘶啞 像被扔在冬天曠野的嬰兒
我覺得那個早晨撿起的 不是楓樹果 而是覆巢的雛鳥 凄慘絕望叫聲 幾十年來只要我想起那個早晨 心中就一陣陣地涌起 對命運深深的恐懼
亂葉溪(之一)
我想不到亂葉溪會如此浩大 我想不到,只不過 下了一夜的雨,亂葉溪 會如此浩大
這就像我想不到 上帝開始創造 就是開始墮落
亂葉溪(之二)
只有大河才能發出 "嘩嘩"的水聲 亂葉溪"叮叮當當"地 流了一夜 亂葉溪小
當黑暗在果馬山谷 升起的時候 當黑暗把果馬山谷 緊緊裹住的時候 我聽見你翻了一個身 小聲地咕噥:好啊 窗外,亂葉溪"叮叮當當"地 流了一夜
一只蒼鷺
一連很多天 一只蒼鷺,在果馬山谷 盤旋,像是在空中 迷了路
很多年后,我還能想起 它像一片葉子飄在空中 嘶啞的叫聲,仍讓我心悸 它讓我一次次地 想到愛情 想到死
果馬河灘
我曾把星星 稱做天空的補丁 現在這些補丁 在閃閃發光 幾只鳥在林子里竊竊私語 又迅速安靜下來 像一道弱光,升起 又熄滅 那些卵石,曬了一天的太陽 現在,它們在吃 從河灘上慢慢升起的黑夜
質問
我在雪地上畫了一條河 一只飛鳥 河流很安靜。鳥也很安靜 河流在安靜地流淌 鳥在安靜地飛翔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 雪地還在,河流還在 但鳥不見了 鳥去哪里了呢
它多像一段潮濕的愛情 借它的消失來質問: 最深的雪,最高遠的天空 最黑暗的心
鐘聲
一個下午柔軟地搭在山頂上 這是你喜歡的白晝 它在你的喉嚨里 欲言又止
山谷是一口深井 粗暴的**在地下 軟弱的饑餓在井口
你捂住樹林的嘆息 捂住大地的心跳,這雙手 更熟悉,也更陌生
我認識山谷的每一條道路 你來,你跟我走 我帶你到白云禪寺的 鐘聲里去
巴音布魯克 ——給張曉鐘
你打馬走進草原 湖泊在左 神山在右 藍天在頭頂上 那個穿花衣服 向你走來的女子 不是叫杰拉古麗 就是叫阿不拉音 在巴音布魯克你成為嬰兒 巴音布魯克是子宮 河流是臍帶 你是一個嬰兒
重生
高原把月亮戴在它的手指上 這夜行者的燈,像倉央嘉措 詩歌的一個音節 掛在山頂 古格王城的眼睛合上了 但目光依然明亮 在片刻的陣雨之中 傾頹的城堡 騰起小小的水霧 煙熏的燭臺,還在 歷數塵世的黑暗 在阿里,在岡波仁齊 神山上的雪在閃爍 并深深灼痛我 但我仍想在它痛苦的光輝里 重新降生一次
壞故事
在山的最深處 里面再無人家 農家樂里只有我一個客人 老板家的一條花狗 有時跑過來看我兩眼 臺風已經來過了 潦草地下了幾點雨 天上有云,月亮昏昧在天空 應付這個山中的黑夜 只有暮色中越來越黑的群山 還有越來越黑的蟬鳴 這一切,讓我的到來 顯得突兀而荒誕 這多像一個說壞了的故事
| 





 QQ好友和群
QQ好友和群 轉播
轉播 分享
分享 淘帖
淘帖 支持
支持 反對
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