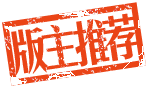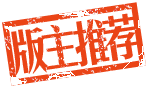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靜川 于 2019-3-26 19:01 編輯
大瓷之美透出詩人的思想深度
——評宋虹的散文詩組章《大瓷之殤》
靜川
詩人就是精神隱喻層面為歷史撰寫碑文的人,想刻意縮小靈魂的閃電,別人也會放大你的內心世界。詩僅僅作為靈魂的關鍵節點,向我們展示各種深入語言的可能性。據此,我們可以探究詩的意義和為后來者重新設定詩的目的和詩的價值。詩人一腔憂憤而滿懷信心,皆源于對“靈魂”的拷問所刻寫的言辭讓歷史發冷或面壁思過。詩不需要是一堆詞匯的羅列,詩需要靈魂的伴隨,讓語言和精神永生。不信你就讀讀我區詩人宋虹的散文詩組章《大瓷之殤》,好詩不需要太多的詞匯堆積,就簡單的“那時候,使用陶器的,都是人民,包括堯舜。”這就足夠讓人敬畏一個詩人的寫作心態。這不是語言大氣,是詩人愛國的志,早就安在心中。“只有火是后來被發現的。//我暫且埋一粒火星在此,關鍵處,讓它燃燒。”(陶:水與火)高手的詩,伏筆這就埋下了。詩人的伏筆,妙在燃燒與瓷,讓后來的瓷,有叮當作響的瓷魂。《大瓷之殤》一共八首,每一首詩,都有自己獨立的內容和靈魂,以及對歷史的評價 “始皇死后,帶走的是陶的兵馬。陶的兵馬不說話,陶的兵馬能忍受一切。兩千多年了,陶的兵馬依然是灰黑色的沉默。//禮崩樂壞,自上而下。”灰黑色的沉默,告訴我們的是“禮崩樂壞,自上而下”,這八個字不難看出,憂國的詩句。 詩寫的大不大氣,還是要看詩人是否有豐富的經歷,生活的沉淀和靈魂里有沒有堅硬骨質。靈魂即詩魂,詩魂里必須要有含鈣很高的骨頭,這很重要。第二首詩《瓷:一個字的誕生》“這是一個被火冶煉了幾千年的字”這個字就是“瓷”瓷就是中國。被火冶煉幾千年的中國,藏著民間高手,“那些衣衫樸舊的窯工,傳遞過冒著青煙的這個字,這個字,烘烤著他們的臉膛,以及臉膛上流淌的汗水……”中國的文明是多少華夏子孫用精湛的手藝和血汗,締結我們為之自豪的古國。 宋虹不僅文筆精湛,他對中國的瓷歷史閱歷深厚。“看天下官窯或民窯,青花或彩釉,都來自于土,水讓它們抱緊、團結,而后成之于火。”這意向是多層意義的,天下無論什么大業,都成之于此,信仰、團結和凝聚力。“現在,我取出一粒火星,讓它燃燒。我看見唐宋元明清的煙火,一直婷婷裊裊。//我們撫摸溫潤的瓷,如同撫摸美人的肌膚,撫摸我們的心。//我們撫摸清冷的瓷,一定會想到火焰,想到火焰般的信仰。”詩人的伏筆,從這里逾越而出,并且最后的“信仰”一詞,還隱匿于詩中。寫詩的人心中必須要有自己的文責和擔當,才能看見“精美的瓷器里,有三百家的窯火,有千萬縷青色的煙,有江南煙雨,有大師和窯工的心血與淚滴。”(景德鎮)這還不夠,詩人的思索是敏銳的,他的目光不僅撫摸于瓷的精美,詩人還看到了“站在遠處的歐洲人,隔著遼闊的大海和蒼茫的群山,仰望瓷器。他們記得昌南,記得瓷器,記得中國。最后,他們把昌南忘了,只把瓷器和中國混為一談。泱泱大國被濃縮為瓷器。”(景德鎮)這才是詩人理解于瓷,叩問于瓷的理性對話——瓷就是中國。 宋虹的詩,感動于人的故事很多,他的詩讓我了解了中國青花瓷的血淚史,在他的詩里,我知道一個叫廖青花的女子,原來青花瓷與她有關。“從秋天出發,去尋找彩料。一場一場的落葉,覆蓋群山,一場一場的落雪,覆蓋群山,也要覆蓋廖青花。廖青花倒在白雪里,她身邊的彩料,終是涂上了瓷器,她的生命也就融進了瓷器。”(青花:一個女子)宋虹的大瓷之殤,絕不是詩人的即興或閑來之筆,只有對瓷熱戀的人,才能知道這大瓷之中的歷史故事,動人心魂。讀著大瓷之殤,就是在讀那些栩栩如生的青花瓷器“青花在廳堂陳列,青花是可以炫耀的美。如果是在盛夏,一盞青花碗里的茶,也有別樣的清涼。”(青花:一個女子)這種對瓷高深度的審美語言,就算我不懂瓷,我也能感受到這種美:青花是藍色的憂傷。 這幾年我作為評論者,我一直在反復讀宋虹的詩,這既是一次次進入到隱秘而深沉的精神生活,也是一次次重逢他在詩歌中對中國瓷歷史加深自己的了解,為解讀這組《大瓷之殤》,樂此不疲。我不斷在這組詩歌文本中感受他對詩或與瓷或與對詩歌賦予神祇般的心靈感召。他對瓷的理解其實就是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他對瓷的那種用心的觸摸,其實也是對中國歷代王朝興衰的感知與發問。“誰見過頭戴烏紗挖泥擔水的人?誰見過身穿紫衣懷抱茅草的人?……青色的瓷也是美的,美得登峰造極,美得驚心動魄。//但我看到,北宋的天下漸漸黑了。”(官窯)詩人的筆鋒是犀利的,詩行里探出詩人的良知,他在瓷里發現了黑暗和憂傷,結尾句非常經典。 在這個詩歌泛濫的時代,能讀到這樣的好詩是幸運的。歌者痛徹,是一種頭顱碰到利器的那種痛切,不是一腳踩在文學的按釘上,痛切的不值得。“大明的船隊滿載著茶葉、絲綢,也載著精美的瓷器……今夜,有一個年輕人就要犧牲了,為了反抗剝削與壓迫。縣衙里,驚堂木在響,兩盆火在燒,一頂鐵帽和一雙鐵靴在火里暗暗地紅。年輕的鄭子木死于暗紅的鐵,死于官商的勾結。什么時候,都需要有獻身的人,這個淳樸的人啊,就是一粒燃燒的火苗。茭草行里的白圍裙,是哀悼一個英雄的半旗。”(民窯)歷朝歷代的消亡,都緣于民怨,國之腐敗與墮落,讓年輕的鄭子木死于暗紅的鐵,死于官商的勾結。直到民間的火燒起來,你撲不滅…… 宋虹的這組詩,每一首的切入點都讓人兩眼發亮,他這是用詩歌審美瓷器,在用美敲擊腐朽。“京城里的薄瓷彩燈,讓皇宮金碧輝煌,也讓皇太子異想天開,他要把瓷燒制成樂器。督陶使快馬傳書,窯工們日夜不息,火焰日夜不息,他們要給皇室燒制瓷笙。十四根管子排列整齊,如一架風琴的鍵,如一首十四行詩?”(云鑼)皇太子的異想天開,就燒掉了多少窯工的命。詩人通過瓷的靈魂高地,俯瞰歷代王朝的腐敗與墮落,有錢人可以異想天開,百姓的命,窯工的血,在黑暗中閃爍。詩歌只與詩人的良知、詞語的發現、存在的真實、內心的挖掘有關。這種理性的詩寫作,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會消除詩的偏執特征。這是一種更具震撼力的寫作,是用頭骨磕痛歷史的一種吶喊! 在宋虹這組詩里,沒有簡單的對“圣詞”的贊詠和烏托邦的理想憧憬,有的只是瓷的血淚與憤怒,瓷的美好和它泣話于詩的精髓。是不是大詩人,我只看他個體經驗的深刻性與內斂的詩語言方式以及吟述性的音樂感所形成的特有質地。這組《大瓷之殤》能夠做到細節的真切和精神氛圍融合,敘事性和抒情性榫接得無跡可尋,嚴整的結構和對歷史與現代社會的發問,但詩人一直忠誠于自己的良知。“這只精美的大瓷破碎了,它來自于內傷,它破碎成無數散片。回望三千年,每一個朝代都有傷心和絕望的人。//我看到,幾千年的水散了,幾千年的火散了。而我埋下的幾粒火星也用完。魂魄不居,那些散片如何聚攏?那些散片即使聚攏,流散的水與火又如何聚攏?//更讓我憂慮的是,人心不古,膺品橫行于市。//我想問一問,是誰把瓷器譯成了中國?這是不是一次錯譯?//誰能給我擔來樸素的土,清澈的水?誰能點燃一場真實的大火,焚燒橫行的敗壞與謊言?我愿意把我最后的血,當作一粒火星,獻給祖國。”(大瓷之殤)這組詩的活力和有效性以及難度不僅是一個寫作者的技藝高超,而且涉及到詩人對瓷的歷史的敏識性,對中國歷史的求真意志的堅持,對詩意和詩人本身靈魂的自覺性。這些酷烈激蕩、讀之身寒令人反思的歷史傷痛,是“大瓷之殤”轉捩的情勢使然,還是詩人一語成讖的現實?!大瓷象征著中國,這組詩大于瓷的審美價值,好詩修于人品,也修于詩人的思想深度。
附詩:《大瓷之殤》
文/宋 虹
1.陶:水與火
我不想說陶,它離我們太遠太遠,有一萬年。我只有一句話,那時候,使用陶器的,都是人民,包括堯舜。
金木水火土,是人類的依靠。金藏在石里,木蕭蕭于群山,土遍存于腳下,而水,則降自于天,更多的在低處。只有火是后來被發現的。
我暫且埋一粒火星在此,關鍵處,讓它燃燒。
舊時咸陽,那個敢自稱皇帝的人,疑心也重,“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寫得一手大篆的李斯,最后都成了破碎的筆畫。此后誰敢說話?始皇死后,帶走的是陶的兵馬。陶的兵馬不說話,陶的兵馬能忍受一切。兩千多年了,陶的兵馬依然是灰黑色的沉默。
禮崩樂壞,自上而下。
2.瓷:一個字的誕生
我們在深厚的大地和時間里挖掘,在仰韶,在馬家窯,在西安半坡,在元大都遺址,我們挖出了不乏精美的青花瓷。我們在漢代,還挖出了一個字:瓷。
這是一個被火冶煉了幾千年的字。這個字一開始藏在民間,那些衣衫樸舊的窯工,傳遞過冒著青煙的這個字,這個字,烘烤著他們的臉膛,以及臉膛上流淌的汗水,以及汗水留下的鹽。
神奇的火,使瓷器發出光彩,這個字從此名揚天下。
看天下官窯或民窯,青花或彩釉,都來自于土,水讓它們抱緊、團結,而后成之于火。升騰的火跳動的火,紅色的焰藍色的焰,燒鑄了瓷的靈魂。
這個字讓我們如此的驕傲。現在,我取出一粒火星,讓它燃燒。我看見唐宋元明清的煙火,一直婷婷裊裊。
我們撫摸溫潤的瓷,如同撫摸美人的肌膚,撫摸我們的心。
我們撫摸清冷的瓷,一定會想到火焰,想到火焰般的信仰。
3.景德鎮
懷玉山脈的江南小鎮,有好山水。毛竹搖曳清風,馬尾松拖動白云,細雨淋濕黑瓦,昌江的波浪輕盈,銀杏的葉片在月光下悉悉索索,是數不清的銀幣。
山坳里的小鎮,從清晨到夜晚,都有人淘洗瓷土,塑土成型,河面上有往來的船影,船上有精美的瓷器,瓷器里,有三百家的窯火,有千萬縷青色的煙,有江南煙雨,有大師和窯工的心血與淚滴。
米粒般的“玲瓏眼”,有你細密的心思游走其間;蟬翼般的“蛋殼瓷”,幾不見胎骨,少一刀嫌厚,多一刀即破。你那明察秋毫的眼神,你那穩如泰山的手,也曾讓古人擔憂“只恐風吹去”。我們需要向大師致敬。
站在遠處的歐洲人,隔著遼闊的大海和蒼茫的群山,仰望瓷器。他們記得昌南,記得瓷器,記得中國。最后,他們把昌南忘了,只把瓷器和中國混為一談。泱泱大國被濃縮為瓷器。
北宋景德年間,朝廷把皇帝的年號給了這個小鎮,小鎮從此叫作景德。
4.青花:一個女子
青花是冷肅的,巨大的青花盛酒,在郊野祭祀祖先,祭祀天地,祭祀神靈。回朝的車馬轔轔,幡旗獵獵,但每一輛馬車上都沒有青花。青花是祭器,青花是容器,青花被遺棄在郊野,蒿草在暗自蓬勃。青花的冷,不帶回宮廷。
一個叫廖青花的女子,從秋天出發,去尋找彩料。一場一場的落葉,覆蓋群山,一場一場的落雪,覆蓋群山,也要覆蓋廖青花。廖青花倒在白雪里,她身邊的彩料,終是涂上了瓷器,她的生命也就融進了瓷器。那一朵朵藍花,成為青花。
那些白多么廣闊,像一場一場的落雪,草木與山水在其上,疏朗而遼闊。還有國畫的抽象和寫意,還有線條的寧靜與奔放,還有釉里紅的暖,讓青花和活人走到了一起。此時,青花在廳堂陳列,青花是可以炫耀的美。如果是在盛夏,一盞青花碗里的茶,也有別樣的清涼。
看遍歷代青花,如果你不知道一個叫廖青花的女子,你不懂瓷。
青花在民間生動,青花是藍色的憂傷。
5.官窯
從北宋一路走來,我心潮激蕩,有多少詩詞豪放,器宇軒昂,即便是婉約做了正統,我依然內心飽滿,崇敬詩篇。
這時候汝窯受寵,道教受寵,淡淡的藍灰色,被叫作天青。青色的瓷,合著帝王的口味。“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寫瘦金體的皇帝,畫工筆花鳥的皇帝,他的權力至高無上,他的美學至高無上。本來要把他的字稱作“瘦筋體”的,聰明的人以“金”易“筋”,這就美了十分。
所謂官窯,也是民燒,誰見過頭戴烏紗挖泥擔水的人?誰見過身穿紫衣懷抱茅草的人?只需下一道圣旨,只需派一個官員,你窯上的火,就要燒出天青的顏色。這些專供朝廷的瓷,閃著青幽的光,讓民間的大師也小心翼翼。
我承認,青色的瓷也是美的,美得登峰造極,美得驚心動魄。
但我看到,北宋的天下漸漸黑了。
6.民窯
最早的火是在民間燒起來的,青煙裊裊,時光裊裊。誰能站在歷史的高處,就會看見磁州窯耀州窯鈞窯定窯,再向南,會看見饒州窯龍泉窯建窯吉州窯,這些人間煙火,被風搖動著涂上天空,天空才有了晚霞的顏色。
火光熄滅的時候,瓷啊,就有了月光般的顏色。沒有散盡的青煙,凝在了月亮上面。
此時,大明的船隊滿載著茶葉、絲綢,也載著精美的瓷器,在茫茫大海之上,滑動出一條柔軟的“絲綢”。
今夜,你的瓷碗里盛著清冷的月色,蕩漾著幾片綠色的葉。
今夜,有一個年輕人就要犧牲了,為了反抗剝削與壓迫。縣衙里,驚堂木在響,兩盆火在燒,一頂鐵帽和一雙鐵靴在火里暗暗地紅。年輕的鄭子木死于暗紅的鐵,死于官商的勾結。什么時候,都需要有獻身的人,這個淳樸的人啊,就是一粒燃燒的火苗。茭草行里的白圍裙,是哀悼一個英雄的半旗。
歷史一次又一次地在說:什么樣的火都是從民間燒起來的。燒起來,你撲不滅,直到燒毀宮廷與城堞。
7.云鑼
京城里的薄瓷彩燈,讓皇宮金碧輝煌,也讓皇太子異想天開,他要把瓷燒制成樂器。督陶使快馬傳書,窯工們日夜不息,火焰日夜不息,他們要給皇室燒制瓷笙。十四根管子排列整齊,如一架風琴的鍵,如一首十四行詩?日夜不息的火燒不成瓷笙,卻燒掉了多少窯工的命,火焰之外,有多少窯工的血,在黑暗中閃爍。太子在京城,依然花天酒地。
瓷是能發出聲音的,比如云鑼。薄厚不一的圓鑼片,是不同的音階,用棒錘敲打,云鑼就會發出美妙動聽的音樂。瓷發出的聲音,是激流的水跌落在石上的聲音,是柔媚的指在古箏上滑動的聲音,是風在銅片上漸行漸遠的聲音……這是瓷的傳奇,樂器的傳奇。瓷的聲音,是微涼的清越的聲音。
瓷是能發出聲音的,你打擊重了,瓷會碎裂,碎裂的聲音更驚心。瓷是有血有淚的,它知道人間冷暖、悲歡離合。這一曲美妙的云鑼,當是人間的絕響。
8.大瓷之殤
這只精美的大瓷破碎了,它來自于內傷,它破碎成無數散片。回望三千年,每一個朝代都有傷心和絕望的人。
我看到,幾千年的水散了,幾千年的火散了。而我埋下的幾粒火星也用完了。魂魄不居,那些散片如何聚攏?那些散片即使聚攏,流散的水與火又如何聚攏?
更讓我憂慮的是,人心不古,膺品橫行于市。
我想問一問,是誰把瓷器譯成了中國?這是不是一次錯譯?
誰能給我擔來樸素的土,清澈的水?誰能點燃一場真實的大火,焚燒橫行的敗壞與謊言?我愿意把我最后的血,當作一粒火星,獻給祖國。
|